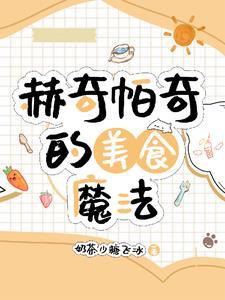大众文学>咸鱼的美食打卡日常92 > 第165章(第1页)
第165章(第1页)
这样切出来的面扁而宽,能挂的住酱,也吸得进汁儿,做拌面是最好不过了。
揉完三盆面,算着时辰许三七捆了蟹上锅蒸,蟹熟下篦子,祝欢和小石头他们来了。
“好香。”祝欢进门忍不住先吸了吸鼻子。
二八酱八分花生两分芝麻,炒过后用石磨磨出来的油香着实醇厚,昨儿许三七去磨坊,因着多掏了几文洗磨钱,磨坊的人便多照看了些,到后头几个伙计帮着装坛,都禁不住打听她卖不卖酱。
卖酱的事她暂且不考虑。
用的食材也不是什么秘方,人闻过便能猜出个几分,真要说哪个是她独一家的,是这和酱的法子。
其中若是用水澥开,酱就稀些,油香味也要减几分,拌面也就差点儿意思了,但当蘸料却是十分合适的,胜在能和别的干料混一个好口感。
“吃过了么?”许三七招呼她们进屋,竹架后摆了张长桌,板凳不够,还是木兰去隔壁借了两条回来。
铺子里的香味再馋人,也没叫东家开肆第一日先给帮工的伙计开灶的道理,祝欢连忙摆手道:“在家吃过了。”
“现在杀鱼?”祝风把几筐黑背鱼从驴车上卸下来拎进屋。
许三七把水缸连着的竹管塞取下来,放了盆水,说:“先片一盆吧。”
鱼肉放过了时辰会失了水分,吃着就不新鲜了,这会儿还没什么客人,不急着备食材。
她才这么想着,铺面上就来了人。
“老板,开肆了?”
是昨儿和沈灼同行的两个护城官,高个儿的叫宋门,脸圆些的是段小远。
许三七用麻布帕子擦了擦手,有些不好意思地招呼:“包子这会儿还没蒸出来,只有面做得快,二位看这”
宋门找了个靠前的桌儿坐下,爽快道:“那就来两碗面。”
昨儿吃过她家的蟹黄包和酸汤,想来其它菜色滋味也不会差。
“好嘞,麻酱拌面两碗。”许三七趁机吆喝。
细软筋道的面下锅,没一会儿就烫熟了,竹筛子捞出来盛碗里,挑两勺麻酱,用小臂长的竹筷迅速翻拌,面挂上酱汁儿,瞧着已经很有食欲了。
祝欢帮着招呼:“大人,蒜水和辣子可要?”
“都成,我两都没什么忌口的。”段小远说。
两碗拌全乎了的麻酱面端上桌,许三七给他们上了一碟胡瓜丝,一碟炒花生,这两样是能自个儿加的,有的人爱吃,有的人嫌。
麻酱拌着黏糊,但端出来的碗身很干净,碗是素净的青花碗,白底的碟子盛着小菜,灶上煮的水往外冒着白气,灶台上摆着几个敦实的大海碗,给人一种铺面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宋门是头回吃没汤水的面,面条揉得实在,一筷子挑起来不断,入口不干,酱汁儿味浓厚,但一点儿不腻,爽口里带着点儿酸,回味有些辣,辣子炒得香却不呛,胡瓜丝作小菜解口,和面一起拌又是另一番风味。
“不错。”段小远几筷子扒拉干净碗里的面,往嘴里丢炸得香脆的盐花生。
他还惦记着昨儿吃过的蟹黄包,私心说再等上一等,反正他两今日就是为的给人捧场来的,轮值的时辰还早,坐一坐也无妨。
刚片出来的鱼片下了锅,宋门点了一碗,问他要不要。
“我留着肚子吃包子。”段小远一门心思等蟹黄包出笼。
街上渐渐有了人气儿,巷口卖蒸饼的小贩断断续续地吆喝起来了,对角的几家铺子也都在门前的梁上吊起了木牌。
“这卖的是什么面?”有人闻着味儿上前打听。
“麻酱拌的。”许三七从竹架后探出头,笑着指给他看,“是我们自家配的酱。”
“怎么卖?”
“原是四文一碗,今儿新开肆,前六碗作彩头,您是头三个。”
打听的人本是图个新鲜来尝尝味儿,也不在意这几个铜子,但沾彩头的说法他爱听,当下便要了一碗,又问店里还有没有别的吃食。
“酸汤煮的鱼片,鱼是今儿一早出海捞的,刚下锅炸。”祝欢抖了抖手里的竹筛,又往后厨张望了两眼,说:“里头在包蟹黄包,若是不赶时辰,可以边吃边等。”
“那就先尝尝酸汤。”
等蟹黄包上屉子蒸,铺面前已经忙不过来了,东西巷南北街四个口都有客人涌进来,有渡口那儿找过来的熟客,也有住在周遭来瞧热闹的人,最多的还是上武馆习早课的武子。
木兰看着摊面前吵吵嚷嚷的人群,舀了瓢水洗手,同许三七说:“面揉了三盆,都切好了,我走了。”
她也得赶去上早课,还得去老头子那儿一趟。
许三七应了一声好,从钱箱里掏了把铜子塞给她,又拧了帕子给她擦脸,说:“你走小门走,午食就到铺面上来吃。”
“我才不走小门。”木兰不听她的,“你怕什么?我又不是三岁。”
家里开食铺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她一点儿不怕人看,更不怕同窗知道。
许三七移开眼,心想她这个年岁的孩子不是都不喜欢被人议论么?
“你累了就歇,忙不过来就去隔壁叫人。”木兰冷着一张脸交代她,谁看了还以为她才是那个做阿姐的。
“知道了。”许三七应得也很快,面上还有几分熟练的乖巧,边说边送她出铺子。
“老板,再来一碗酸汤。”有客人急着点菜。
“去吧。”木兰冲她摆摆手,迎着一些人的视线顺着巷路往武馆去。
蟹黄包刚出笼就卖空一屉,老面皮裹着满满的蟹膏,段小远咬着流汁儿的包子,庆幸自个儿早来了,不然这场面,挤破了头也买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