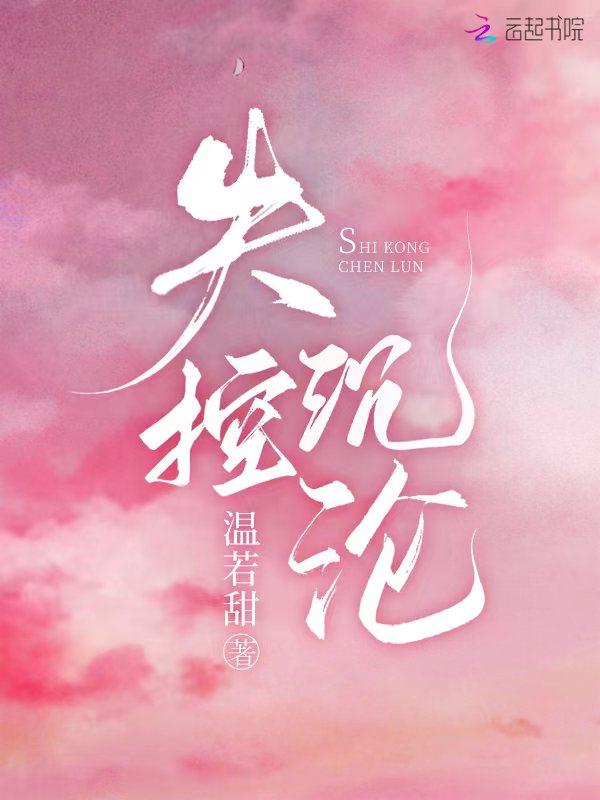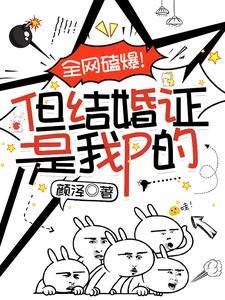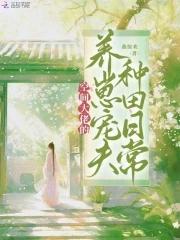大众文学>走眼一直跳怎么回事 > 第66章 拧巴(第1页)
第66章 拧巴(第1页)
回到酒店,黎风闲吃了两粒退烧药,迟迟不见有睡意,他只好打开电脑改下后天要用的PPT。
原计划需要他在九十分钟内讲完昆曲数百年来的兴衰和变更,以浣纱记为起点,到申遗以后出现的“新美学”、趋近现代化的舞台布局等,事无巨细全都要讲。
但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落地F国后,他们收到主办方通知,说九十分钟太赶了,可以酌情删减两到三个不那么重要的部分。至于什么是“不那么重要”,对方又吭唧不出一个标准答案,让他们按心情来就好。
黎风闲一坐就是一下午。等他改订出第二个版本,日头早下山了,天色脱去一层,高楼挂着的霓虹招牌节节亮起。
将PPT发给主办方后,门铃两长一短有规律地响起。
“我还以为你在睡觉。”林振山换了套正装,提着个保温袋站门口,“醒着正好,吃点东西吧。”
“不饿。”黎风闲按开房灯,垂投下来的光亮得扎眼,他拧动开关调暗几度,才稍稍适应下来。
“不饿也要吃。”保温袋咚一声搁桌上,林振山从里头拿出三菜一汤,还有一瓶开胃现榨的果汁,“今晚你就别用去了,吃完好好睡一觉,睡不着就吃片安眠药。”
菜是餐厅大厨做的中餐,两素一荤,林振山拍拍椅子:“过来,吃不下也吃两口,就当是陪我吃吧。”
黎风闲拿他没办法,只好烧一壶热水帮林振山洗个杯子出来。
离晚场交流活动还有两个多小时,林振山这会很是松闲,靠在吧台左看看右瞧瞧,又从钱夹里翻出一张名片。
“实在难受就给这个人打电话,他是医生,中国人,袁溪的表弟。”知道黎风闲从小就不爱看医生,林振山索性将这人往“自家”方向提,大旗先挂出去,至少顺耳些,总比某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听起来亲切。
“嗯。”黎风闲无所可否。
草草解决完这顿晚饭,林振山窝在沙发里晾肚皮,两根手指托着本历尽沧桑的小型笔记本——
封皮焦黄曲翘,软不拉耷的,像在水里泡过一遍。
内页全用白线缝在一起,是本手工钉装的线装书,能看出整理者是个考究人。
幸好时间这把杀猪刀削皮不伤肉,内文字体依然清晰有致。
“讲什么不好非要讲紫钗记?现在都没几个剧团演全本了,用的还是八几年的录像。”林振山惋叹一声,“老谈这人真是……轴得要死。”
“天虹的?”黎风闲选择性接收前半段话。
“嗯,天虹第一次出国演出,唱的就是折柳阳关。”林振山把笔记本盖到腿上,仰起脖子,凝注顶上飞碟一样的烟感警报器。
“那会儿袁溪和搭档天天吵架,从早到晚不带歇的,妆造能吵,走位能吵,吸气慢了半秒也能吵。两个人一碰面就犯病,谁劝都不好使。后来团长觉得他们吵架吵得挺有创意的,就搬张椅子过去,一边听他们吵架一边改剧本。”
“那时候没人看好天虹,都说我们是观光团,到欧洲走个过场而已,凭什么能拿奖?连我们自己都这么想。几十个剧团参赛,凭什么是我们?出发前谁都不敢提比赛两个字,就当是场普通演出,尽力就行。可咱们团长说……说天虹能拿奖,一定能拿奖。”
林振山万感齐上,指关节抵在眉心压了压:“可惜没等我们回来他老人家就走了,留下这么一个剧本,媒体夸他的话一句没听着……早知道就不在欧洲庆功了,说不定能赶上最后一面,圆他个心愿。”
黎风闲清理完桌面,坐下,给林振山倒了杯水:“但你们把他的心愿保护得很好。”
林振山笑开:“折柳阳关?”
黎风闲摇头道:“是天虹。”
停了一息,林振山才愔愔接过水杯,别过头啜一口:“所以风闲,你别听老谈扯那些大道理。他们那圈人就喜欢搞血统论。血脉一定要正、要纯,要师出有门,就算你唱得再好,贡献再多,叫不出名字的一律打成野班子,说什么都是邪门歪道,有失正统。真按他们那套标准来搞传承——”
“说真的,还传个什么劲儿啊?早晚不都得绝后?”
喝完一杯水,林振山起身散步消食,绕着房间内沿走:“你也看见了,这几年讲座开得越来越多,从大学开到高中,从国内开到国外,内容大差不差,都是些理论上的东西——什么是气口啊,什么是正字正音,什么是以四声协五音……”
“但想教会老百姓‘看戏’,光靠事先教育是不够的,很多内核不是一本书,一段录像就能讲明白,得让他们亲自去看、去感受。那么问题来了,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呢?”
绕了房间一圈,林振山到窗台前站定,摆弄起主办方送的塑料小花,像发现什么新玩具,笑着拈了拈花瓣:“早年曲高和寡的亏我们吃了,没钱、没观众、没新人。一场演出百来块工资,二级八百*,一级一千*。到八十年代末,转行的人越来越多,不用养家糊口还好说,有家有孩子的,谁愿意跟你这么个熬法?这可是戏曲史上明确记载的事实。”
“后来国家开始投放资源,救活了一批项目,也有剧团主动复排传统戏了……结果呢?还是没观众啊。没观众就没市场,演员也是要吃饭的,梦想吹得再好听也不顶用。为少数人服务是没前途的,昆曲之所以没落,是因为不愿意与时俱进。像老谈那种,他是个理论家,他不懂演员是什么心态,他不知道申请经费,请人排戏是多麻烦的事儿,他只知道这是联合国给的荣誉,你们不能动它。”
黎风闲看着他的背影,眇眇忽忽,像回到二十年前,那时林振山也是这样站在窗边给他讲剧团里发生的事情,天南海北,再艰厄的苦难他都可以挂着笑说出来,变成一个个逗趣的黑色幽默。
有时候林振山会望着剧团荒芜的后院发呆,他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就叫一声林叔叔,等林振山转身,继续眉飞眼笑地说他的故事。
天虹和闲庭不一样,他们团长半路出家,手头经费拮据,成立初期走了不少弯路,人脉也没好好疏通,演出全靠募款和赞助。
林振山师承名家,父母都是生意人,小时候养尊处优,不愁吃穿,殊不知离开家门后,曾经最激扬的雄心壮志一朝成了最不值钱的白糖二两——
说到嘴边是甜的,但不管饱。
只有走过这条路,才感悟一切理想主义的词汇都是象牙塔里的高墙。
所以林振山经常告诉他,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但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如果毅力不足以让你支撑下去……那就尝试让自己爱上它。
黎风闲走到他身旁,除去发间变白,林振山还是当年那个首屈一指的巾生。年轻时养成的生活习性年复一年地保留下来,银灰色西装裹在他挺实端方的身躯上,嗓音苍劲,带着点锉磨出来的颗粒感,不显老态,倒有种另类的潇洒。
“住我对门的老太太今年九十六岁了,没读过书,字都认不全,但能哼哼两句《思凡》,我问她从哪儿学的,她说没学过,是跟电视里的人唱的。”林振山把塑料小花递给黎风闲,“去听讲座的不一定有人家老太太学得快。传承嘛,先想好怎么传下去才是正道,上上电视上上电影又不是坏事,非得上长安大戏院才叫正统?”
“我明白。”黎风闲接过小花,分量轻飘飘,盆底还有点割手,塑料得名副其实。他转了转花盆,不知道碰到什么开关,花身左右一摆,细管里居然冒出片新叶子。
“好兆头。”林振山管不住手,逗猫似的勾勾叶子,“你看,这就叫枝繁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