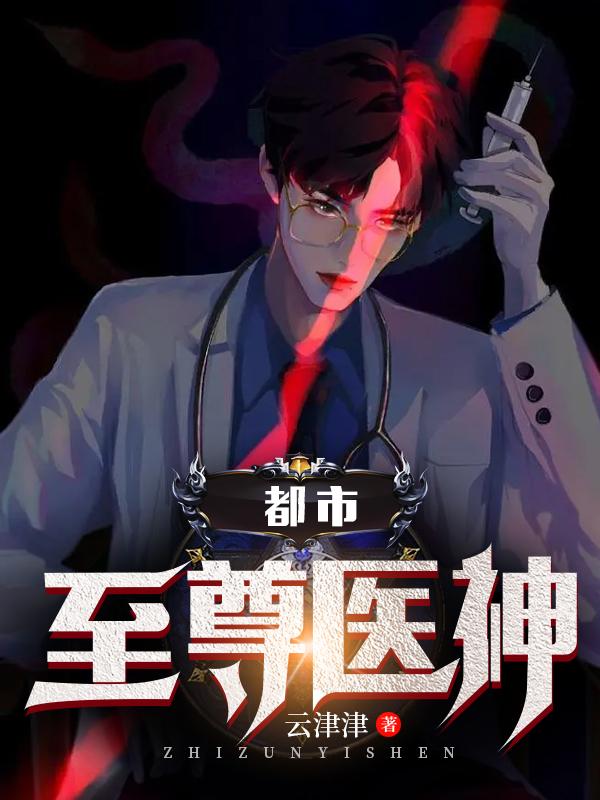大众文学>综武侠我虽然叫冯蘅格格党 > 年岁 只可惜谁也没注意(第2页)
年岁 只可惜谁也没注意(第2页)
孙不二年纪比周伯通还要大上两岁,不仅是她,全真七子中大部分人年纪都比他大,若论年纪,他实在与普通弟子们相差无几,几乎是同岁人,但按照辈分来,却是比他们足足高出一辈来。现如今,冯蘅也是见怪不怪了。
周伯通对着孙不二敷衍的扯了扯嘴角後,便欢喜的拉着她来到外面,向她展示这偌大的粥棚,得意道:“你看,我这搭建的不错吧?别看结构简单,但能防风防雨!”
“道长昨夜已观天象,今天无风无雨呢。”
“防患于未然嘛。”他挠挠头,尴尬道,却见她原本一脸认真的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才知道自己又被耍了。
不过现在没时间拌嘴,百姓们见粥桶和道士们已到位,不消片刻已涌动而出,大排长队起来,哪怕不是家境贫寒丶缺衣少食者,也想通过这福粥沾沾道教神仙的庇护之运。为了不让这些人在这麽冷的天久候,施粥工作便马不停蹄的立刻开始了。冯蘅占据一棚间,挽起袖子,便干起活来。
她不是食堂阿姨,拿着长勺的手可不会抖。用赤豆杂米熬制的浓稠的“口数粥”被满满的打入一个个伸来的碗中,这种粥不仅能果腹,还被认为具有“辟瘟”之用,所以有着“大杓轑铛分口数,疫鬼闻香走无处”的说法。一桶见底,一桶又来,虽然腰酸胳膊累,但她一句抱怨喊累都没有,始终勤勤恳恳的工作。
“快说,谢谢姐姐。”
接过粥的女子视线朝下,冯蘅才瞧见粥桶前方有个矮小个的小孩子,那孩子一手牵着身边的母亲,一边好奇的看向自己,被母亲提醒後,他听话的说道:“谢谢仙女姐姐。”
“真可爱!”太会说话了,冯蘅喜笑颜开,忙将腰间悬挂的用草药制成的香囊摘下,挂在了小孩的脖子上,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这个送给你,希望你健健康康的长大,不要生病。”
即使没有反馈,她所做也是心甘情愿的,但如果有称赞,那会获得更多的动力和快乐,人嘛,就是这样。
眼看着那对母子离开,她嘴角仍挂着窃喜的笑容,周伯通将又一桶粥擡上了桌子,趁机凑了过来,对着她说道:“原来你也会喜欢这种话。”
她美滋滋的挑眉道:“哪种话?分明是实话!”
“嗯嗯,实话实话,”他绕到了她另一边,帮着递馒头,“不是阿蘅,是仙女姐姐!”
“哎呀,你又不是小朋友,不准你这麽喊我!”她羞恼的瞪了他一眼,从他嘴里说出来可就不是实话,而只是调侃了。
周伯通哈哈大笑起来。
嘻嘻哈哈吵吵闹闹之间,时间悄然流逝。排至街尾的人群已经没有再增加的趋势,此时已差不多申时。
冯蘅实在是累的腰都挺不直,手臂擡不起来了,便被周伯通强行拉走,换了个年轻弟子接替,两人坐一旁长条凳子上小作休憩。
喝着水的工夫,自街道这头走来三五成群的一队人,各个顶着夸张的妆容和吓人的装扮,走两步跳两步,嘴里还哼哼唧唧着模糊不清的咒语一类的曲调,一时之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冯蘅眼瞧着稀奇有趣,起身站在路边,连连张望,直到那群人消失于视野才恋恋不舍的回来。
周伯通告诉她,这仪式名为“驱傩”,是当地习俗,意在驱走疫鬼,保佑来年顺遂平安。冯蘅点点头,其实也猜到了大概。这个时代的人们多数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过一生,不生病对他们来说是顶重要的事情,所以才会有如此多的驱疫驱鬼的活动。
“你若早几日下山,还能看到‘跳竈王’呢!那更热闹。”
“跳竈王?”
“对,腊月里,乞丐们会几人一伍,装扮成竈公丶竈婆,每个人手上拿着一根竹竿,去各家门口讨要,给钱也行,给米也可,还有些会直接进人家里面去,不给不走!”
“还能这样?”她惊奇感叹。
所谓“竈神人媚将人媚,毕竟钱从囊底来”,除了健康不生病,能糊口吃饱饭更为重要,而竈台承担了此象征意义。有竈王爷保佑,来年一定不会挨饿,所以这群乞讨者不仅不会被赶走,还会被各家笑脸相迎。他还跟她讲述着,腊月里还有“接玉皇”丶“烧松盆”丶“照田财”丶“送年盘”等习俗活动,她当听新鲜故事般听得津津有味。
“阿蘅的家乡呢?习俗与我们这边大不同吗?”他忍不住问道,怎见她一副听到什麽都大为新奇的模样,五湖四海过年差别竟有如此大吗?
她笑了笑:“有共通之处,但总体说来的确大不相同。”置办年货丶挂桃符丶亲友间互相馈赠丶大扫除一类自然是古今无异的,但要说差别在哪,那必然是挤春运丶等春晚看春晚骂春晚,以及“全国人民端起热气腾腾的饺子”了……
施粥已尽尾声,街道附近的家家户户也相继关门闭户之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鞭炮声,噼里啪啦一阵响,一种粗糙的热闹氛围为这人间的一整年划下了利落的句号。
周伯通看着被鞭炮声吓得忙捂着耳朵却笑个不停的冯蘅,视线无法挪移一寸,嘴角竟无意识也溢出浅浅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