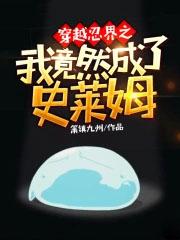大众文学>替嫁医妃王爷他心动了免费阅读 > 第127章 兵危边境(第1页)
第127章 兵危边境(第1页)
金銮殿上,众臣屏息以待。方才贵妃与王妃之争才刚起头,未曾想一份“十万火急”的军报骤然闯入,将原本的宫廷权斗暂时撼动。皇帝翻阅这份密函,眉头越皱越深,俨然看见危机四伏。
“北境边防统领来信说,近期外邦多股势力纠集,在边关一带骚扰劫掠。局部冲突已扩大,恐将演变成全面战事。”皇帝声音低沉,将此军情公之于殿上所有大臣,“朕不想战事失控,需尽快派得力将领前往镇压。兵部,枢密院,你们可有良策?”
兵部尚书即刻站出,神色凝重:“陛下,北境防线虽有驻军,但因近期朝中政局欠稳,物资粮草调配不及时,若敌方联合更多外部势力,恐怕守军难以支撑。建议火增兵,并派得力王爷或亲信大将坐镇指挥。”
皇帝轻抚龙案,口气森然:“朕也有此意。只是,这座北境向来牵连甚广……当年顾家便是镇守此地,后来因所谓‘谋逆’案被清剿。眼下驻扎边关的老将也所剩不多。若朕派太子前去,未免离京过远;若派九王爷,朝臣又会不会质疑他‘拥兵自重’?你们都说说看。”
此言一出,群臣面面相觑,心里都清楚:皇帝故意把太子、九王爷这两条路都摆在台面,看众人的反应。太子若远征边关,朝中局势更不稳定;九王爷若离开京城,万一真能掌握兵权,在边关培植势力,岂不对皇帝与太子形成新的威胁?这道抉择深藏凶险。
一时间无人敢先表态,唯有空气里弥漫着紧张气息。
太子萧明烨轻咳,试探性地道:“父皇,儿臣身为储君,自当分忧。若父皇愿意让儿臣挂帅出征,儿臣绝无推辞之理。不过……京中时局微妙,儿臣若远离,恐有宵小趁机捣乱。还请父皇明鉴。”
这番表态,说得滴水不漏:既表示自己愿意承担统帅之责,又暗示若他离京,会造成权力空缺,九王爷可能图谋不轨。他的话分明意在逼皇帝不要轻易下这种“远征令”。
萧靖寒站在侧列,微微敛眉。看太子既不想离京,也不想让自己掌握边关兵权,那么皇帝究竟会如何取舍?此时不等他自请或表态,兵部尚书又一次奏道:“陛下,卑职倒有一策:可否让朝中大将随军坐镇,另派皇室王爷作为监军或钦差辅助?这样既避免朝廷核心权力空虚,也能维系对军中的掌控。”
皇帝沉吟不语。所谓“另派大将坐镇,王爷辅佐”,看似折中,但能否拿出合适人选,才是关键。如今朝中老成持重的宿将,多数因当年顾家案的清洗而凋零,剩下的要么与太子交好,要么倾向九王爷。而顾家案尚未翻,北境更牵连这桩旧事,实在棘手。
气氛再度凝滞之际,一名武将模样的老臣出班,声如洪钟:“陛下,北境形势凶险,不能再拖。顾家当年谋逆的传闻,如今尚未坐实。可顾家当年镇守边关之功,却是实打实的。老臣愚见,如果现今朝中能有一位熟悉北境军务的皇室之人,携带军令出征,或能尽快平息战火。”
他说完,场上安静少顷,又有几位与顾家曾来往的老臣暗暗附和:是啊,当年顾家在北境名声极盛,旧部残余或许有助于平定当前骚动。朝廷若能示好“顾家系”兵士,重新收拢军心,边关就不至于陷入混乱。
这番话带着某种“为顾家昭雪”的暗示,太子听在耳里极其不快,皇帝却若有所思。
萧靖寒脑中灵光一闪:若真能重启对北境旧部的激励或收编,一方面能制止战乱,另一方面也能收集更多顾家旧案证据。然而自己若主动请缨,是否会引起皇帝与太子疑心?可事到如今,他不得不一试。
正当他踌躇之际,皇帝忽然抬眼看向他,淡淡问道:“九王爷,你在边关长大,对那片土地多少有些了解。如今战事突起,你可愿前往?”
萧靖寒心神猛地一震,暗道:皇帝果然还在衡量我与太子的平衡。自己若此刻表示拒绝,就等于放弃机会,也显得没有担当;若表示愿意领兵,势必要面临太子与朝中保守派的掣肘。“既是父皇有此问,儿臣岂敢推诿?”他先含蓄回答,随后又拱手补充,“只是儿臣以往病体缠身,朝堂中或有质疑——望父皇三思。”
皇帝眯起眼睛,似在打量萧靖寒:“朕知道你身体已大有好转,多次见你奔波并无不适。若你真有心替朕分忧,就别再用病体做借口。”
萧靖寒心中一凛,皇帝这话颇有试探意味。若再遮掩“病症”,恐被皇帝怀疑。于是他索性一咬牙,躬身道:“儿臣愿意出征,为朝廷稳定尽绵薄之力。”
这无疑是一种表态,也是一种赌注。果然,太子面色一沉,还没等皇帝再说话,他就冷笑:“九弟素来没掌过兵权,贸然领军会否不妥?边关战事凶险,非得老成谋略之人坐镇。更何况,顾家残部对你心怀好感,一旦与外敌接触,会不会生什么‘里应外合’的诡异局面?”
此言一出,不少大臣心知太子在给九王爷挖坑:若九王爷在边关遇上顾家旧部,极可能形成一支私兵,对皇权构成威胁。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萧靖寒却毫不退让:“若父皇下旨,儿臣自当唯命是从。边境将帅不可缺,儿臣可辅助朝中资深大将。不会让太子殿下担心‘兵权旁落’。”
太子被呛得眼神更冷:“哼,你最好记住自己有几分本事。到时若兵败如山倒,可不要给朝廷添乱。”
皇帝听着二人言锋暗斗,脸上不动声色:“朕自有安排。传朕旨意:即刻调集禁军精锐三千,与各地驻军共组北征之师。以老将齐远为主帅,九王爷为监军,官衔从二品。太子与兵部、枢密院留京调度粮草,随时配合。”
一句话,堵住了太子的口,也定了萧靖寒出征的地位:他不是主帅,但以监军之名行使皇命,能有一定话语权,却不至于完全掌握军权,也避免了太子口中的“威胁”。
萧靖寒迅拜领:“儿臣遵旨。”
太子也被迫应声:“儿臣领命,会安排好后勤支援。”
皇帝环视满殿:“此次战事事关重大,不容有失。齐远将军乃宿将,曾多年驻边关;九王爷年轻有谋略,此番随军也好学习兵事。务必短期内驱逐外敌,保我北境安稳。若有人懈怠,休怪朕治罪!”
群臣齐呼:“臣等谨遵圣谕。”
金銮殿内最后的指令敲定后,皇帝带着兵部、枢密院几个要员去内宫继续商讨具体细节,太子与萧靖寒亦随侍在侧。直到快近正午,君臣商议大体完毕,这才分别退下。等走出宫门时,萧靖寒只觉人困马乏,一颗心却愈焦躁:自己即将离京出征,而林轻歌那边与顾家案子尚未了结,贵妃、太子仍暗中虎视眈眈。若一旦走了,会不会让她独自面对险境?
他深吸一口气,对身旁暗卫道:“先回府,我要见王妃。”
太子在后面遥遥注视,一边与随行党羽低语:“九王爷看样子心有顾虑。等他离京,林轻歌便是囊中之物,也难逃我们的掌控。”
随行党羽点头:“殿下高明。只要九王爷走开,顾家案再无后劲。那时,您可徐徐除掉林轻歌,彻底断了顾家翻案的念想。”
太子眼里闪过狠色:“但北境一事也不能小觑。九王爷若是真在边关立功,到时名望更盛,父皇或许对他另眼相看。绝不可让他顺利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