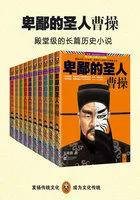大众文学>吾乃孝悌仁义汉太子也免费 > 第609章(第1页)
第609章(第1页)
夷人被汉人骗惯了,再多的花言巧语,都抵不过刘盈那双真诚的大眼睛,以及他捧出的户籍律令。
刘盈拉着夷人首领,一条一条向他们解说,哪些律令能保障他们的权利。即使夷人都知道,律令这玩意儿,在权贵面前比擦屁股的缎子还不如,可有总比没有诚意更大。
关中的边患,便暂时安宁了。
边患能不能多安宁一段时间,要看中原最终的胜利者是谁。
刘盈派出了自己全部的兵力,在袁绍的冀州和曹操的豫州征战。
虽然他自己的后勤运输很有压力,但成为战场的冀州和豫州,已经毫无有秩序的后勤可言。
袁绍的军队已经在捡河蚌和狩猎补充军粮,曹操部分军中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案。
继承天师道的张燕和创立五斗米教的张鲁张修,即使在刘盈的命令下不以宗教为基础,也能轻易煽动人心。
大不了,再喊一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不过这个时候,还是以东汉末年本就存在的民谣做为口号,更能引起共鸣。
刘盈根据后世的润色,将这首民谣最后一句更改,让它在中原各地唱响。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拿着粗劣武器的百姓,仿佛自杀般地冲向了袁绍和曹操的征粮军队。
一如秦末拿着竹竿的黔首,也如十几年前将黄巾裹在头上的那群庶民。
崤山以东的豪族震怒不已。
张盈,他都不怕吗?
“若我为帝,定再约法三章,兴文景之治!”
刘盈每到一处,就许诺免一年徭役赋税。粮草充足的刘盈的军队,对沿路村庄所剩不多的糠麸丝毫不取。
就凭借着这些豪族看不懂的小恩小惠,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空口保证,刘盈所到之处,百姓无不箪食壶浆相迎,人人唯恐刘盈不为帝。
刘盈恍然。
曾经他与阿父一同进入关中。同样的举措,同样的情景。
或许那时的他还年幼,或许那时承担所有期盼的是他的父亲,刘盈虽激动自豪,感触却不深。
至少没有深到脸上许久没有笑容的程度。
原来是这样啊。
这就是阿父肩上的压力。
刘盈骑在马上,可以轻易看清站在地上的人那蕴含了太多的期盼,以至于五官都扭曲了的脸庞。
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多卑微,多天真。
可这时的人,除了将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还能做什么?
已经长大的刘盈,早已经明了“汉圣宗圣皇帝”这个谥号庙号有多不合规矩。
中原文化总是含蓄的,汉人王朝即使再期盼圣君,除非追封先祖,否则不会用“圣”来作为庙号。
而评价皇帝一生的“谥号”,也没有一个人能担得单独一个“圣”字。
至于复字的谥号,那便已经泛滥,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