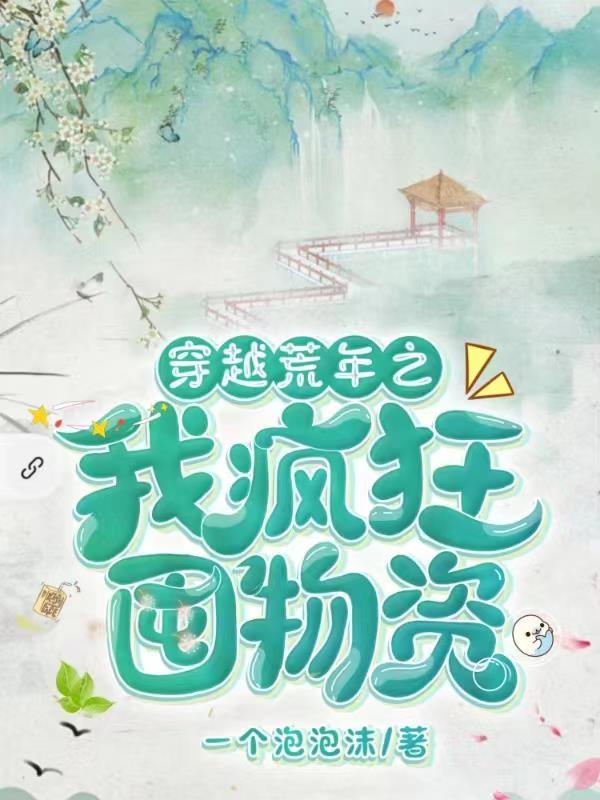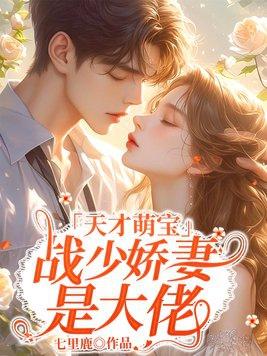大众文学>西柏林怎么与西德交流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要去找斯塔西。”
“那我就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莱纳不再说话,俯下身,额头顶着交握的双手。安德烈以为他会哭,但实际上并没有。汉斯极少谈起莱纳,安德烈之前误以为这对兄弟并不亲密,现在看来更像是汉斯在保护这个弟弟,把莱纳放在军情六处无法触及的地方。可以理解,但安德烈有任务要完成,他拍了拍莱纳的肩膀,让年轻人抬起头来。
“听着,你现在要做的是回家去,彻底忘记这件事,好吗?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答应过汉斯,如果他发生意外,我会照顾你。”汉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但反正莱纳已经没有机会确认了,“我当然不可能替代真正的兄弟,但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来找我,不要再去‘麻雀’咖啡厅,斯塔西长期监视那个地方。到西柏林去,找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联邦邮政,跟接线员说你要寄一封‘去法国的挂号信,但是写着地址的纸被水泡了,门牌号化开了,不过姓名是清楚的,能寄到吗?’。必须按照这个顺序讲,好吗?去法国的挂号信,没了门牌号,但名字很清楚,重复一次给我听。”
“一封去法国的挂号信,但是地址泡了水,看不清门牌号,但名字是清楚的。然后问能不能寄到。”
“正确。很好,他们听到之后就会转接给我,如果我刚好不在,就留个口信,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找我,我会找你。”
“好的。”莱纳声音微弱,看起来有些恍惚。
“回家去吧。”安德烈把他拉起来,整理了一下莱纳的外套,“忘了汉斯,也忘掉我们今晚说过的话,好好生活。”
莱纳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摇摇头,脚步沉重地离开客房。门的铰链定时上油,开的时候没有声音,但老旧的地板就没有办法了。再轻的脚步也会引起一连串刺耳的嘎吱声,安德烈听着莱纳走下楼梯,踱到窗边,拉开布帘,看着汉斯的弟弟独自穿过路灯和路灯之间的丛丛阴影,没有人跟踪他,街道空荡荡的。莱纳拉紧了外套,弓着肩膀,背影很快就被建筑物挡住,看不见了。小麻雀已经放回森林里了。
第五章
沃格尔家的父亲,理查德,七岁那年被送去当木匠学徒,十六岁就开始在家具作坊里帮忙。他很擅长做衣柜和斗橱,今天的周日旧货市场里说不定能找到沃格尔先生做的雕花橱柜。和许多古典小说情节一样,他最后娶了木匠师傅的女儿,准备继承家具作坊。沃格尔夫妇的长子汉斯1924年出生。第二个孩子是女儿,葛楚德,未满一岁就因为白喉夭折了。到了1930年秋天,最小的儿子莱纳再次把他们变成一个四口之家。
不管从什么角度观察,木匠沃格尔一家都是平凡的普通市民,平凡程度甚至低于均值。年轻的沃格尔先生和太太都不关心家门外的世界,街上大吵大闹的青年团成员?不了谢谢。被纵火的犹太教堂?那是别人的事。兴登堡总统?国会选举?一个坐过牢但不知为何霸占了德国权力高地的油漆匠?谁有空看这些麻烦事呢。只要桌上还有面包,家具店还接得到订单,木匠沃格尔先生就可以快活地过他的平凡日子。
木匠沃格尔去世的那天是个湿漉漉的春日。他开着借来的车运送一个刚做好的衣橱,那是个漂亮的衣橱,橡木做的,打磨得像镜面一样光滑,购买者的姓名首字母缩写藏在鸢尾花浮雕里。一对富有的夫妇订造了这个衣橱,要求送到度夏用的乡间大宅。
衣橱最终没有到达目的地。汽车被过路人发现的时候,侧翻在森林里,不远处是公路的转弯处,木匠和同去的雕刻师已经没有呼吸了,橡木衣橱被甩出车厢,撞上了一棵树,摔裂了。警方调查开始得很慢,结束得很快,毫无疑问,车在转弯的时候打滑,顺着满是泥浆的斜坡滚进树林,司机和乘客也许没有当场毙命,但从伤势看来,就算当时马上送医,活下来的机会也不大。
沃格尔太太卖掉了家具作坊和里面的设备,搬到了日后将会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利滕贝格,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住进一间更小的公寓,靠父母和丈夫留下来的一点积蓄度日,偶尔做些缝纫之类的零工。战争开始之后生活反而好过了一些,母亲到工厂里缝制士兵制服,汉斯参加了国防军,纯粹是为了那份固定的薪饷。随着德国在海外节节胜利,他们得到的好处更多了,几乎每个月都能分到整箱的食物和酒,有时还有肥皂、布料和巧克力。普通人的好日子仿佛再次回来了。
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一切又被击碎了。盟军投下来的炸弹在稍远处爆炸,摧毁了面包店,炸开了沃格尔家朝向街道的那面墙,满地狼藉,客厅里全是碎玻璃和砖块,父亲亲手做的橱柜被弹片打穿,留下一个足以放进拳头的大洞。汉斯两周前被调去守卫郊区的一个军火库,至今没有回来,无法确定是不是还活着。母亲和莱纳收拾了稍微值钱的东西,在火车桥的桥洞下睡了几个星期,那里拥挤不堪,满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从自己家里逃出来,有的抱着匆匆抢救出来的微薄财物,有的只有一张旧毯子,所有人都一脸尘土,眼神呆滞,好像从梦里惊醒,发现自己一脚踩进更深的噩梦里。
汉斯终究还是回来了,深夜里,怕得发抖,像只老鼠。他穿着一件捡来的衬衫,上面染着喷溅状的血迹,散发出粪便和腐肉的臭味。因为害怕被盟军士兵认出,他早就扔了国防军制服,尽管母亲没有说什么,但两个儿子都能看出她始终没有原谅这个举动。沃格尔一家回到了损毁的公寓里,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把帆布和床单挂在墙壁本应该在的地方,勉强应付,直到苏联人领着工程师来拆除了危房,把他们重新安置到匆忙建起的水泥盒子里为止。
母亲和汉斯之间隐隐约约的矛盾在汉斯决定去德意志邮政工作的时候彻底露出了血淋淋的裂口。沃格尔太太把柏林的占领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视作绝对的仇敌,禁止汉斯和这里面的任何一方扯上关系,而汉斯完全不能理解母亲的想法,他渴望过上“正常”的生活,如果苏联人能带来这种生活,那也无所谓。十五岁的莱纳夹在他们两个中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避免同时受到双方的叱责,只好躲起来。
汉斯是在1949年圣诞节前搬走的,事先没有预兆,某个早上忽然就提着箱子走了。这间逼仄昏暗的公寓里就只剩下莱纳和母亲。莱纳开始问一些以前不敢开口的问题,关于父亲,战争,柏林,汉斯在战时做的事。母亲不愿意谈论这一切,话题一旦越过1945年的界线,她就声称头晕,要到卧室里躺下。
母亲的房间现在空着。她去世之后,莱纳就没有进去过,更别说收拾遗物了。他打开灯,在门口站了一会,目光落在发黄的床单上,然后是梳妆台上的首饰盒和梳子,椅子上放着没看完的书,一截用作书签的明黄缎带从页间露出。母亲喜欢读书,汉斯却完全相反。莱纳关上灯,脱掉外套,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
他本来躺下了,但又想起了陌生人给他看的文件,重新坐起来,拧亮台灯,用毯子盖过头,双手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地盯着毛毯的纹路。照片里的尸体已经没有脸了,幸好复印件是黑白的,那些撕裂的肉和碎骨看上去是一团乱糟糟的黑影。尸体可以是任何人,但从衣服和钱包看来,肯定就是汉斯。他的手又开始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愤怒。莱纳攥紧了床单,强迫自己回想小时候家具作坊楼上的厨房,那里既明亮又温暖,有糖浆和牛油的甜蜜气味。餐桌上有汉斯的木头玩具和吃了一半的甜杏果酱。父亲在楼下切割木板,手锯的声音富有规律,莱纳闭上眼睛,让呼吸重新平稳下来。
然而那个自称安德烈的陌生人可信吗?文件可以伪造,人经常说谎,也许汉斯还活着,被英国人囚禁了起来,但他们没理由要花费精力这么做。莱纳不认为自己值得任何人花时间。
他掀开毯子,仰躺着,看着天花板,转而琢磨安德烈。这人给他的感觉无从形容,不像莱纳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第一眼看上去就值得信任,但又隐隐令人不安,笑起来的时候尤其,好像安德烈早在莱纳出生之前就认识他,而且知道许多个和莱纳密切相关的笑话,但是打定主意不说出来。莱纳思忖着这个陌生人从哪里来,他的德语太流利,不像外国人,但也没有好到能确凿地说就是本地人。也许是南部某处来的,奥地利边境附近的某一个无名村镇。他为什么会和英国人混在一起?汉斯又为什么和他混在一起?
莱纳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翻了个身,蜷缩起来,在客厅的钟敲响午夜之前就睡着了,忘记熄灭台灯。
——
他尝试实践安德烈给的建议,“彻底忘记这件事”。然而“这件事”盘踞在脑海里,像条蟒蛇,吞食别的思绪,膨胀得越来越大,直至占满了他清醒着的每一个小时。汉斯在德意志邮政的同事不再张贴寻人启事,甚至不愿意谈论汉斯这个人,也躲着莱纳,似乎已经猜出了汉斯的下场。和安德烈见面之后的一个星期里,莱纳不管走到哪里都觉得有人在看自己,甚至留意到同一个穿风衣的男人总在上下班路上出没,他没有明目张胆地跟踪莱纳,但很明显不是个友善的路人。莱纳无法确定到底是斯塔西真的在盯梢,还是自己已经疯了。
有一次他差点忍不住跑进“麻雀”咖啡店去找安德烈。从使馆下班之后他骑着自行车去了柏林西北面的法国占领区,停在咖啡店的前一个路口。坐在电线杆旁边的报童上下打量他,右手搭在绑着皮带的木箱子上,估量这个瘦弱的年轻人有没有钱买一包高卢牌香烟,很快断定莱纳不是潜在顾客,移开了目光。
就是在这个时候,莱纳又看见了穿风衣的男人,那人戴着灰色毛线帽,很可能因为头发不剩多少了。察觉到莱纳的目光,那个人走开了,沿着街道往前,快到一栋布满弹孔的废弃房子的时候拐进小巷里。
莱纳骑着车走了,飞快掠过“麻雀”咖啡店。落地玻璃窗的反光让他看不清楚里面有什么人,这一瞬间的走神害他差点撞上一个提着篮子的老妇,莱纳大声道歉,用力蹬踩踏板,转过街角,向东边逃去。
他没有打电话,觉得还不是时候,至于什么时候才合适,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安德烈给他留了一扇关着的门,虽然关着,但是没上锁,他得亲自去打开。他有多想弄明白哥哥身上发生了什么,就有多害怕门后面藏着的未明危险。越衡量得失,莱纳就越气恼安德烈给他留了选择权。
公寓里安静得可怕,甚至能听清楚挂钟走动的声音。莱纳把沾着肉汁的餐盘放进水槽里,双手扶着水槽边缘,透过灰蒙蒙的窗户看对面布满黑色水渍的砖墙,过了差不多五分钟,他大步走出厨房,抓起外套,出门了,骑着车在暮色中前往西柏林。他选了跨过英国占领区边界之后看见的第一个电话亭,把自行车丢在地上,关上门,从口袋里掏出零钱,几个硬币从手指之间滑落,叮叮当当掉到地上,他弯腰把它们捡起来,塞进电话投币孔里,拨了联邦邮政的号码,很容易找,就写在号码簿第一页。
可是突如其来的勇气也消失得很快,莱纳用力握紧听筒,听着对面问了三次“有什么可以帮你吗?要转接哪里?”,没有说话,砰地挂上电话,多余的零钱叮叮当当掉落,他连看都没有看,推开门,扶起自行车,沿着来时的路回去了。
第六章
刚才我说莱纳挂断电话的时候,你感到失望吗?心里有没有冒出一点轻蔑的苗头?你在想,“可怜的胆小鬼,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可是我们都经历过那个东德男孩所经历的一切,犹豫不决,恐惧,怀疑,困惑。每个人都是从同一扇门跨进来的,你,我,安德烈,刚开始都这样。
这也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对一个情报官来说。我们喜欢故事的开头,我们看着这个新来的目标,这只带有斑纹的蛋,猜它孵化之后的样子。有时候你得到一条蛇,有时候是聪明的猎鹰,有时候只是一只可有可无的鹌鹑罢了。
安德烈没有奢望得到猎鹰,他可能只想要一个汉斯·沃格尔的替代品,活着的,而且更容易操纵。莱纳在母亲和长兄的影子里长大,他习惯被推着走。汉斯是一个有效的受力点,只要安德烈一直施加压力,不难把莱纳推到他想要的地方去。
因此安德烈不明白为什么整整八天过去了,莱纳还是杳无音讯。也许他把小麻雀放得太远了,以至于莱纳没有折返的勇气。又或者汉斯作为一个哥哥,在莱纳心里终究没有“不惹麻烦”来得重要。这多少有些尴尬,安德烈在电报里向霍恩斯比吹嘘的聪慧计谋,连第一步都没有走出去。
这一个多星期里,安德烈总共见了两个潜在的线人,都是通过他在东德警察局认识的人搭上的,一个是在斯塔西第十司工作的秘书,五十二岁了,是那种穿着款式古旧的碎花上衣、佩戴珍珠耳环的年长女士,非常不引人注目,是理想的耳目,可惜她接触到的文件只有无聊至极的行政乱麻,充满了预算案、申请表和不同部门之间心胸狭窄的斗嘴记录。第二个候选人是卖地毯的,每三个月往来一次柏林和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情报人员十分熟络,多年来贿赂海关的结果。然而安德烈看不出他能在柏林发挥什么作用,只能把地毯商人转介给伊斯坦布尔情报站。
他需要地下线缆分布图。这些电缆就在他每天走过的街道下面,承载着莫斯科和红军东柏林司令部的秘密,像条奔流不息的地下河,离他这么近,但就是没办法舀到哪怕一勺水。霍恩斯比昨天深夜飞抵柏林,直接坐车到弗伦街那栋红砖建筑,和中情局柏林行动处的人开会,安德烈并没有受到邀请,不过第二天一早被霍恩斯比带到古伦森林“散步”,行动处处长对柏林市内两个地点很感兴趣,一个在勃兰登堡门附近,一个在火车站附近,他想知道要是在这两个地方“建造一些东西”而又“不引人注意”,是不是不切实际。安德烈回答当然是的,思忖着伦敦和华盛顿到底是彻底绝望了还是发疯了,竟然打算在市中心开挖隧道。
两人在一个路边小摊买了香肠当午餐,乘车返回奥林匹克体育馆。就在汽车到最后一个街口的时候,安德烈瞥见了路边的一辆自行车,以及站在自行车旁边的人,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坐直了。霍恩斯比当然留意到了,转过头来,循着安德烈的视线看去,扫视着行人道,询问下属是什么让他如此惊讶。
“不,没什么。认错人了,还以为看见了美国大使馆的科尔先生,你记得他吗?新年酒会喝醉之后吐在苏联贸易代表身上的那个。”
“可能再过十年才能忘记。但科尔不是半年前就回国了吗?”
“对,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看错。我在这里下车就可以了,想去买包烟。”
车在路边停下,离体育馆门口的岗哨还有五六十米,离自行车不到二十米。安德烈下来了,转身走向不远处的杂货店,买了火柴和香烟,假装挑选货架上的巧克力,借助一个玻璃糖罐观察霍恩斯比的车,直到它开出视线范围,才走出商店,径直走向自行车和自行车的主人。
莱纳看见了他,露出羞怯的笑容,似乎想挥手,但可能被安德烈的脸色吓到了,收回去,用指甲来回刮擦自行车把手。情报官大步走近,手按在年轻人的肩胛骨中间,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赶离奥林匹克体育馆。两人快步穿过马路,安德烈带着莱纳往人最多的地方钻,尽量躲避可能存在的监视,一边回忆附近有哪个安全地点,可以暂时安置小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