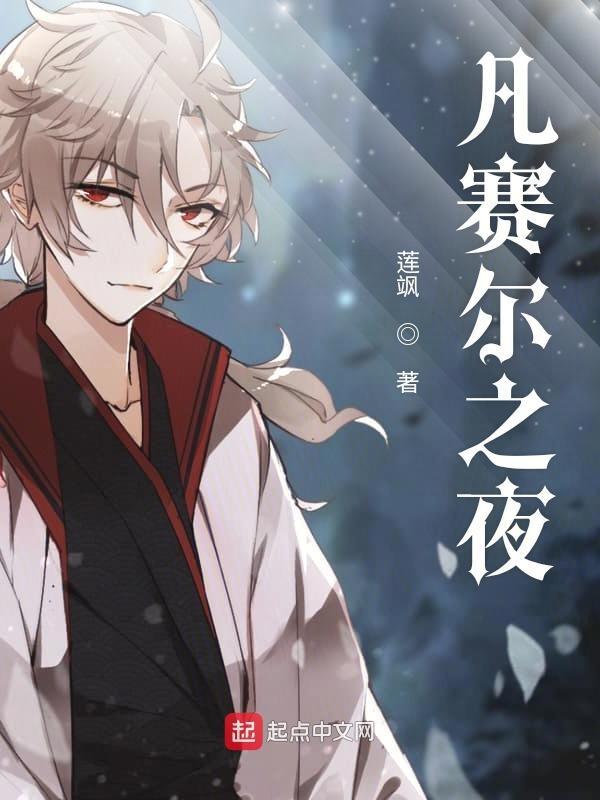大众文学>为婢结局 > 第52章 春猎(第1页)
第52章 春猎(第1页)
我说:“她来寻事的。”
但凡秦芳若不在这种时候急着上门来嘚瑟,我又怎么会去跟她起争执?
“她找的莲心,没找你,”萧律不以为意的道:“她也不能拿你如何。”
意思是能忍则忍。
在他眼里,只要秦芳若没杀了我,就是小事。
可偏偏如此,我才更难受。明知道旁人是因我而被欺辱,我却无能为力。
“把莲心送走吧,”我想了想,说,“她家在田县,送她回家也好。”
萧律说:“哪怕没有莲心,还会有其他人。”
我说:“不用有其他人,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这种处境,又何必再拖个无辜之人下水?活反正我也都会干,干习惯了的。
我以为送走莲心是件举手之劳的小事,他没理由拒绝。
可是他说:“这个不行。”
“为什么?”
萧律抬起手,将我鬓边丝捋到耳后。
“好了,我会同芳若说一声,这院子里的人不能动。不过前提是,你得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无外乎安分守己,忍气吞声,讨他欢心。
我才这时才后知后觉的明白,正是因为我在意莲心的生死,他才偏偏要把人留在我身边,以此来束缚我的手脚,叫我从此三思而后行。
“该做什么,”我麻木的说:“我不知道。”
他视线停在我小腹处。
“你知道的。”
……
萧律嘴上说任由我去审巧儿,可等我到私牢中,巧儿已经断了气。
死得干脆,并不是遍体鳞伤的那种死法。
我走出私牢,葫芦等在外头。
他脸色在寒风中吹得略显苍白。
“姑娘,对你来说一无所知才是好的,你想要对付王妃,无异于蝼蚁撼树啊。”
我附和说:“是啊。”
我心中知道是蝼蚁撼树,徒劳无功一场,只能惹人笑话罢了。
可什么都不做,心中不安又几乎能击溃我。
葫芦叹口气,嗓音略微沙哑。
“二两白银买个丫鬟,三两便能买个姿色尚佳的。权贵们随手一个喝茶的白玉杯也是三两……景姑娘,碎个茶杯罢了,也是主子们花钱买来的,哪里轮得到我们这些奴才置喙?”
话是在劝我,可我隐隐约约从他语气里听出悲哀痛心的滋味。
他是身强力壮的侍卫,比丫鬟值钱些,却也没贵上多少。
我迟迟说不出什么话来,沉默片刻,道:“这辈子吃够了苦,下辈子总能投个好人家了,不再是二三两的命。”
实在无可奈何,只能拿这种话来哄哄人,得些安慰也好。
……
这个冬,是我那么多年来,最不愁吃穿,却最难熬的冬。
每过一日,我便在砖上刻下一笔。
不知萧律是怎么去秦芳若那边打的招呼,她这两个月没来找过我麻烦。
哪怕我去园子晒太阳,她遥遥见了我也转身便走。
日子算得上清净。
冬去春来,枯地上有了绿意,莲心把厚袄狐裘之类都收拾起来,忙得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