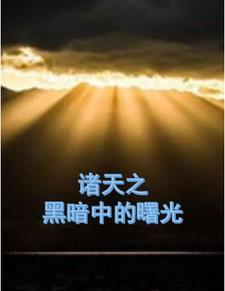大众文学>凤呜朝歌 > 第404章(第1页)
第404章(第1页)
拓跋昉在函谷道设伏,被胤鸾君识破,扫除障碍后,率军从容不迫地逼进五十里。
拓跋昉退至灵宝,列阵再御,又败。其帐下兵士在漫山遍野竖起的大治军旗与敌军高呼中心志崩溃,弃甲而奔。
眼前是势不可挡的凤翚军,黄河岸边,是迂回登岸包抄的敌军侧翼。
拓跋昉空有调兵遣将之能,却敌不过大势,受围之下,拔剑横于颈前,仰天大恸:“娘娘!臣有负所托,无颜面见先君与陛下,在此谢罪!”
左右慌忙抢剑,不知谁的血抹在刃上,一片血色斑驳。
“国师休存死志,京中尚有禁军,不如还京,再图后计!”
拓跋昉似哭似笑地望着被云遮住的惨淡日光。若说他在对战胤鸾君之前,还存有一丝侥幸,等真正见识过对面的悍不畏死,他便知赫连之败并非偶然。
“哪里还有后计了……”
·
九月,秋风烈,褚盘克下许昌,阮伏鲸攻破虎牢。
神泽三年春,所向披靡的四路大军合围洛阳,终于在北邙山下会师。
不同的州府番旗迎着风缕,竖立如林,共同点是皆隶属于一位君主的治下。
一支膘肥马壮的骑兵如滚滚黑云席卷过千金堰,为首将领身长体硕,英气逼人。他一直驰到那面最高峨耸立的大纛前,凝望着一层层护军拱卫的最中央,那名身披蛟龙锦,头戴宝莲冠,玉容含光,如日降临的女子,眼眶湿热,坠镫下马。
将军以军礼叩拜,声音有些颤抖:“臣阮伏鲸,恭迎圣主!陛下圣明神武,号令如一,统驭九州,江山清平!”
谢澜安见到表兄,霜雪容颜倏地浮出一笑,下马亲自扶起他。
“表兄,别来无恙。”
自她身后,将士齐齐下马。
胤奚长腿扫过马鞍,走到阮伏鲸面前打量他肤色几眼,含笑:“阮大将军攻破虎牢雄关,成前人未成之业,威风了得。”
两年前泗水边,阮伏鲸让他叫自己“阮大将军”的戏谑,这小子还记着呢。
阮伏鲸回视胤奚,看着气质比从前更为沉敛的男儿,真心实意道:“有你在陛下身边,我安心很多。”
说罢,他目光与列队中的褚盘四目交错。
褚氏少主冷白的脸上没有忌恨之色,至少表面上没有,平静地向对方点了点头。
谢丰年立枪与阮伏鲸打声招呼,他手中那杆百战不折的长枪,正是阮伏鲸当年赠他的那一杆。
胤、谢、阮、褚,这四位日后在功臣阁悬像立传的开国四将,都曾活在父辈或主家的荣光和庇佑之下、也曾失去过自己的亲兵、陷入过九死一生的绝境。他们受着谢澜安的指引,一路行来,终于聚集在此,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一致,那便是破开近在咫尺的最后一道城门与宫门,捍卫他们认定的明主,会当凌绝顶。
不是侵凌,而是回家!
“给我三日,臣定为陛下拿下金墉城!”阮伏鲸抱拳请战。
坐落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便如同金陵的石头城,皆是为保护国都而建的军事堡垒。
大军临城,拓跋氏之所以还不开城出降,便是靠着此城负隅顽抗。
谢澜安首肯。料峭风色中,她转目望向护城河环绕的那座黛瓦古城,与城头上漆黑肃穆的垛口。
胤奚知她所想,拍了拍青骢马辔,“既是回家,怎能不走正门,阊阖门交给我。”
语气就如讨一碗酒喝一样平常。
谢澜安看向他,昂扬一笑:“仰仗胤爷了。”
她故意在人前叫出这个称呼,胤奚在那片明眸轻睐的眼波下,身体发热,气血鼓荡。
男人勾唇俯首,周身锋芒毕露:“愿为陛下效劳。”
那年自作主张冒雨直奔泗北的路上,年轻人不知自己生死,却已暗中立誓:胤衰奴会向世人证明,他从来不是谢含灵的软肋,而是铠甲。
……
“南人打来了!”
“是、是那个女皇帝,她纠集了二十万大军,已到城外!”
洛阳内城阴云密布,百姓如惊弓之鸟,有人躲在紧锁的家宅中求神拜佛,有人极惊之下冲到混乱的街面上,试图从哪条城郊小道找一条逃匿的生路。
可城池四门都已被治军堵住,哪里还能逃脱?
尽管南朝女旁一再令节使传话,入城后不伤百姓,不烧杀劫掠,可百姓们依旧恐惧。
仿若蒙上了一层阴影的皇宫殿阁,灯树倒地,鹦鹩惊飞,到处可见宫娥太监瑟瑟躲藏的身影。
比宫外百姓更害怕的,正是朝中的朱紫大臣。他们安享逸乐太多年,等到大祸临头,才忆起当年尉朝先君攻入洛阳城时烧杀奸淫,屠城立威,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往事。
风水轮流转,谁知道南军破城后会如何报复?
听说那位女帝,最是睚眦必报。
“太后娘娘……不如,降吧?”
有人绝望之下恳求尉迟太后。
半个月前尉帝驾崩,皇太子仓促继位,可大臣们仍习惯于有事启奏太后。
此日,尉迟太后穿着一袭玄青回鹘纹素服,唇色浅淡,周身无饰。她转动两只微眍的眼眸,看向跪在庭殿中间,从函谷突围逃回京城的拓跋昉。
拓跋昉神色憔悴,哑声说道:“大尉有今日,臣未能纠改国戚贪墨军饷,引得六镇叛变,一罪也;未能识鉴妖道,劝阻圣人,二罪也;领兵不敌贼军,令河山沦丧,三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