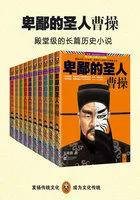大众文学>凤朝鸣庭 > 第397章(第1页)
第397章(第1页)
朦胧的烛晕笼在两具交叠的胴体上,白得不相伯仲。谢澜安不忍看,手指却已摸到了那些伤痕。
有的深,有的浅,有的弯曲,有的瘢痕轻凸。
她问胤奚这些伤如何受的,胤奚在昏光里带着一丝自陋的卑怯,凝目观察谢澜安的神色,摇头淡道:“早就不疼了,能为陛下的山河永固尽一份力,是衰奴之幸。”
他不敢说用打下的疆土当作给她的聘礼这种话,女郎自己便能策动千军,身边从来不缺为她效命的人才。
只要她帝位坐得更稳一分,于愿足矣。
“你别嫌弃我。”
谢澜安已经分不清他在故意邀宠,还是真的这么想,她以嘴唇代替手指,充满怜惜地吻过他的每一枚勋章。
“这样,好受点吗?”
怎么会嫌弃呢,疼他还来不及。
胤奚闭眼享受,尾巴翘得又高又直:“那我只可惜伤处还不够多。”
肚脐上方被咬了一口。
胤奚吃笑一声,顾怜他的玉手继续向下,胤奚忽然声音发紧,喟叹:“陛下……那里可不是伤疤……”
谢澜安脸上发热,他想得挺美……胤奚忽然把她拉上来,眼里淀着沉甸甸的欲潮。
他咬她的耳朵:“陛下,我在军中学到一种不会有孕的法子——要不要试?”
他的语气,活像一只妖艳的精魅引诱她吃下一颗甜美甘果,吃了,便能到达极乐世界。
想到男人堆里那些荤素不忌的浑话,谢澜安又气又笑,用力将人推倒,翻身坐上去,按着男人坚硬的胸膛:“看来胤爷除了打仗做扇子,也没闲着呀。”
长长的黑发顺着她光滑肩头滑落,遮住寸缕不着的春光。
胤奚静了一瞬,心跳在谢澜安掌下擂动。
“你,要在上面?”
他惊异得忘了尊称。
“不然呢?”谢澜安挑眸。
女皇陛下如此理所当然,胤将军在极度惊喜下绷紧了身体,桃花眼潋滟生澜:“来啊。”
来,也是要讲技巧的。谢澜安前后挪蹭调整,将身下的人当成第一次学骑射时试骑的马,涓流濡过礁石。
胤奚手抓床褥,喉结上汗滴滚下,一点不敢打断她的兴致。
高风永夜,飞檐下的宝铎细碎轻响,香暖锦帐中,只有呼吸的绵绵微声。
谢澜安不好往下看,余光甩了眼胤奚。
这一眼,直接被他隐忍风流的神气勾得心跳失序。
她不怕疼,却不得其法。
胤奚被折磨得命都快给她了,“……坐下去。”
“啰嗦什么!”
胤奚叹息一声,猛地坐起来勾弯女皇陛下的一对膝窝,上身俯压到最低,低下头。
世上最软的两样事物相接研磨,终于开启了通往欢愉的前奏。谢澜安头低脚高地向后仰倒,云鬓渌发像黑夜里的曼陀罗,绽放在浅红地莲枝纹的锦被上。
从床头换到床尾,女子压抑轻吟,犹嘴硬说:“我可以,刚刚马上就行了……”
“嗯……陛下厉害。”胤奚抵着舌尖,声音黏腻,“是臣等不及,打断了陛下雅兴。”
身下的雪如波浪涌动,他抬起头,拱起后背覆上去,如同野兽慵懒向前爬行。“陛下,看着我。”
男人以最强有力的跪姿,挺腰送出自己。
几乎没感到疼痛,谢澜安失神地望着墨发垂散的胤奚,下意识松开咬唇的贝齿:“阿奴……”
这是她此后能发出的唯一完整的字音。
烛花噼啪地落,仙人承露盘更漏声声,银虬泄水。
胤奚腰似水鳗,眼含媚丝,凭着本能丁送,挖掘巢中每一寸藏有珍奇的宝地。
谢澜安眼波半敛,头皮发麻,指甲抠进他后背,那些凸起不平的伤痕皆成了助兴的标记。
她最后的底线,是不能叫出声。
“女郎,哭出来。”
她闷喘的样子让胤奚受不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心底种了劣根,想让那张冷潋清傲的脸上沾满情玉。
是沾满。
他匍匐在最高洁的人身上,一下下让她发出最迷乱的声音。她禁锢着他,那软弱的禁地也无可后退地任由他逞凶。这种反差让胤奚的身心快活到无法承载。
银漏滴干,在一声沉喘中,胤奚喷发在红浪被间。
这就是他口中的办法,留给谢澜安的余韵却久久未歇。
发丝被汗水沾湿的女子,一身肌肤透出粉玉般的色泽。她听见胤奚连名带姓地叫她,带着原始的野性,在灵魂上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