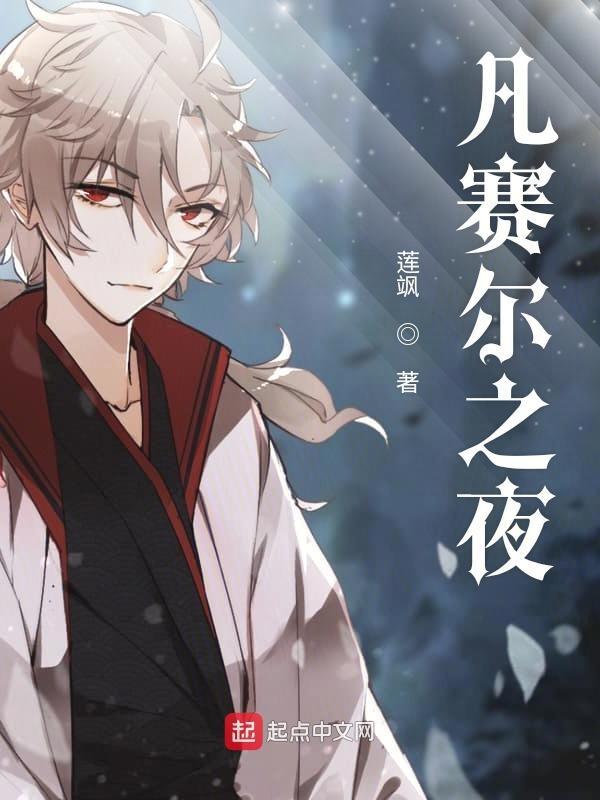大众文学>花月为客全文免费笔趣阁免费阅读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好,我听门主的,」沈夜雪稳步走近,面色静冷,朝男子低缓相言,「可我有一请求,望门主能救下无樾。他跟随我多年,我不愿见他因我丧命。」
皓腕被握上的一霎,一股力道将她扯入清怀,全身微僵,感受盈盈松雪气息环绕,她轻阖了眼。
轻巧锁此姝色在怀,他仅是哼笑一声,薄唇附於她耳旁,却不碰她:「筋脉尽断,浑身断骨三十二处,你应知他活不了。」
「是吗……救不下吗……」
心上有悬石落入了沉沉死寂,她忽觉无措,不觉恍惚起来。
「可我刚才还觉着,你是能救的……」沈夜雪任其轻拥,喃喃了几语,忽而转眸,「如若不然,你又是如何……」
话语一顿,她没了底气。
「你又是如何能活至今日……」
他中了花月散都能安然无事,无樾的伤势他定有医治之法,若非这般,费力从坊中带上一将死之人,不像他作风。
然而当她回看时,所见的是他满面凝重之色。
仿佛他历经的,是一段不堪忍受的苦楚,不愿回想,不愿诉说。
离声默然良久,倏然言道:「睡吧,先不想了。」
「我还未服侍门主,怎就先睡了?」原本轻环着她的手莫名放了开,沈夜雪不解,脱口便问。
问出口的一刻,她才觉自己疯了。
她这不是在引火烧身,咎由自取……
他闻语再度无言,沉寂许久,平静回道:「那你脱了。」
「是。」
恨不得将那一语的每一字都收回……沈夜雪唯觉窘迫,可又念着总会有这一时,便伸手缓慢地解起裳扣来。
解衣之馀,一只木盒从袖中掉落,她欲俯身拾起,指尖触及木匣时微顿,随後将此物还於眼前人。
「这玉石还你,它本该是你的。」
清眉不禁紧锁了起,离声迟疑接过:「你未给他?」
此举她也不甚明了,莞尔勾唇,随性道着:「不明何故,我忽然就不想给了。」
或许给了公子,也无法将其讨好,也无法与那孤冷身影成上大婚,她所做一切皆为徒劳,一切皆为她自欺欺人的幻念。
居於花月坊,她仍会日日担惊受怕,所受的恩宠仍会被他人夺去。
如是一想,她便不愿给了。
不如还於相赠之人,全当是她的赔罪。
衣裳层层褪尽,唯剩一件单薄寝衣着於身上,墨发如瀑披散,她起身轻阖房门,而後轻柔地为此人解下衣袍。
她垂目不敢望他,静默无词,埋头硬解着暗扣。
因她从未解过男子锦袍,此般费了好大气力,尤显着她的笨拙。
曾作为花月坊最得宠的女子,还是名扬千里的花魁,愚钝成这模样,定是要被讥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