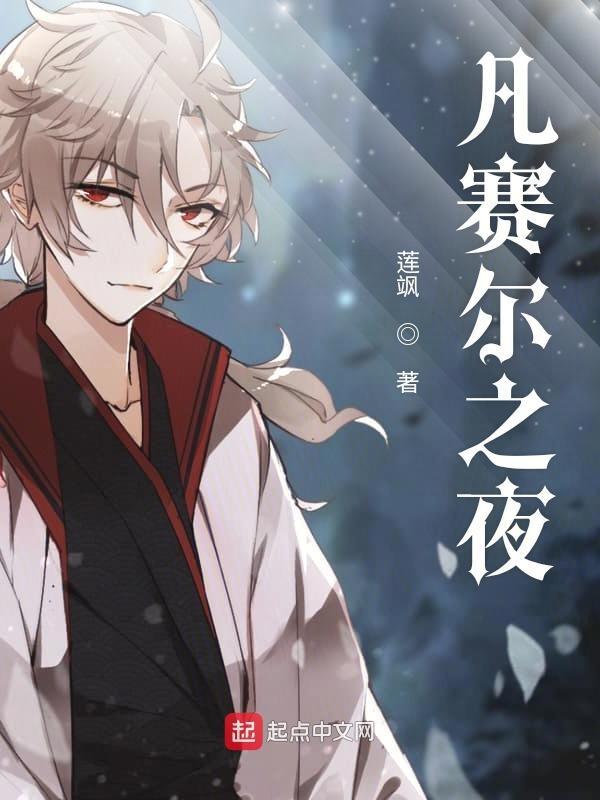大众文学>秘方的意思 > 第73章(第1页)
第73章(第1页)
这康仁寿早不走晚不走,偏偏要和她前后脚离开,当真是有种说不出的可恶。
那樊统似乎知道她在烦恼什么,又慢悠悠地问道。
“酉正初刻前后,那离宵禁也就还有不到半个时辰了。不知康先生是如何离开的?可是叫了下人备好马车来接?”
那郭管事仿佛就在等这一问,立刻恭顺地继续汇报道。
“康先生也是没想到小姐的病情起色如此之快,因是临时要走,便没有提前叫药堂伙计驾车来接,说走河上、搭船便好,就叫了府上正得闲的老秦送一段路,还付了对方三十文钱。这些府上小厮和码头路过的船工都可作证。”
康仁寿上了秦三友的船?这一切未免有些离奇。可眼下秦三友不在这里,她也无法当面质问清楚,只能努力集中精神分辨得到的消息,试图找到反击的机会。
“就算如此,为何咬定就是在我阿翁的船上出了事?回春堂应当也并不在河道边上,康先生也有可能是下船后、在回药堂的路上出的事。”
这回换了樊统身旁那一直沉默的小胡子开口、正是那掾史曹进。
“回禀大人,今早我便派人寻到那秦三友、将他的船扣了。搜寻一番后,便在船底发现了血迹。依下官来看,这女子虽然柔弱却是做惯苦工的,那送菜的老翁更是身体硬朗,想来若是将人藏在船上又抛尸河中,倒也不需要多大的力气。”
好一个做惯苦工、好一个身体硬朗。
似她和老秦这般辛劳之人,唯一的一点欣慰之处便是这副饿不死、熬不坏的身体了,可如今竟然有人借此反证她有能力杀人,当真可悲可笑至极。
秦九叶突然笑了,声音中少了些惶恐多了些愤怒。
“康先生是临时起意要离府的,我与阿翁如何提前计划此事?难不成若是康先生不走,我们便要闯进苏府将人绑走?”
此话一出,整个府衙后院当下便是一阵沉默。
可沉默过后,是比方才更加激烈的一轮反扑,那曹进对她话语中的愤怒置若罔闻,声音更加严厉。
“何须提前计划?就是见财起意、恶念顿生犯下的案子!”
大难临头,此时不搏何时搏?此刻秦九叶早已将方到此处时的胆怯丢到了一旁,整个人几乎从地上站了起来。
“敢问大人能否确认那船中血迹就是人血?我阿翁前些日子曾为苏府送过几只活鸡,许是东家又要他帮忙运了什么……”
惊堂木“啪”地一声响,樊统随之拍案而起。
“一派胡言!死到临头还在狡辩,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
他“上刑”两个字还未说出口,一道声音接踵而至。
“我倒是觉得,这位秦掌柜说得有些在理。”
樊统愕然抬头,只见邱陵不知何时已快步进入这庭中。
他似乎来得很是匆忙,身上还穿着那件黑色甲衣。绿水映出他修长挺拔的身形,好似一把笔直的墨尺,将那屋瓦间的金碧之色分做两截。
樊统先前一直斜倚着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坐直了,挣扎了片刻,他还是勉强起身跨出那树荫半步行礼道。
“见过督护。什么风将您吹来了,这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案,怎敢劳您大驾呢……”
“原来樊大人口中的上不了台面,是这个意思。”年轻督护那双眼望了过来,眼神中是一股无法令人忽视的压迫感,“也不知我若在场,今日这事是否能上得了台面。”
好端端地,究竟为何每次他都要当众给他难堪呢?
樊大人心中说不出的怨念,但一张老脸仍挂着笑,慢吞吞地摩挲着手里的惊堂木。
“督护说笑了,她只是个嫌犯,一个平日里便作奸犯科的贼子,此刻说得话怎能尽信呢?她说她昨日早康仁寿一步离开苏府,有谁可以作证?又许是在哪处藏着等待时机……”
“这我倒是可以作证。”
邱陵的声音一字一板地传来,秦九叶却不敢抬头。
她又想起了苏府中的那一幕,实在分不清眼前的人是否真的是来帮她的。
仿佛为了印证她此刻所想一般,下一刻对方便继续说道。
“樊大人坐这郡守的位子也有十余年了,当知道要想定人的罪,需得有证据。不如换我来问。”沾了雨水的靴子停在秦九叶面前,靴子的主人声音毫无起伏道,“听闻秦掌柜昨日出城后便回到了丁翁村住处,一直到天明府衙派人来找才离开,期间除了我在亥时前后拜访过,可有其他人能够证明你确实没有离开果然居?”
秦九叶有苦说不出,只喃喃道。
“有倒是有,不过……”
不过他人不在这里,也不能来这里。
然而就在她犹豫着不能开口之时,她身后大门的方向传来一阵响动,一名衙役急匆匆来报。
“启禀大人,门外有个人硬是要闯进来,我本想将他拦下,可与他同行的还有苏家的……”
他话还未说完,另一道声音由远而近、自雨雾中倏然而至。
“官爷莫急,我只是来寻人的。”
秦九叶茫然回头,只见身后正对府衙大门的石阶下,立着个撑伞的瘦高身影。
下一刻,那伞檐微微抬起,露出一双浅褐色的眼睛。
“阿姊,天落雨了。你没带伞,我来接你。”
细雨沐禾
九皋城一年中恨不能有两三百天都在下雨,这其中要数入夏时的雨水最难熬。
春的反复缠绵还未离开,夏的潮湿燥热已经袭来。天一会一个样,雨水一会多一会少,穿多了也不是、穿少了也不是。出门走上几步,鞋底子就潮了,一整天都不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