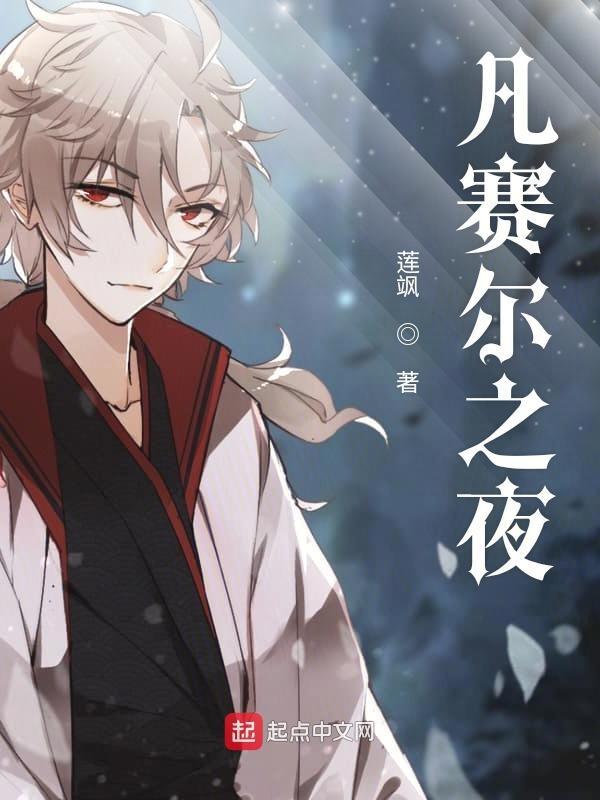大众文学>南华曲金牙太太免费 > 第40章(第1页)
第40章(第1页)
柴荣一愣,语气不由自主的温和了许多,道:“朕许你自辩,若是无辜,朕必还你清白;若真有其事……朕亦不能姑息。“
秦妃盈盈而出,拜倒在地上,宽大的粉色裙摆像一朵娇嫩欲滴的蔷薇,在脚边绽放。她娓娓叙述,声音像是微风拂过水面,划出不惊不奇的波澜:“臣妾出身江南,母国战败,以妾为贡女,跋涉而来。娘家、父兄、亲友皆在千里之外。因此,自入宫第一日起,臣妾便知,与其它妃嫔姐妹相比,臣妾唯有陛下一人可依靠。皇后指责臣妾行为乖张,臣妾不敢辩驳,然而究其缘由,不过是因为臣妾恪守了真诚二字。“她眼波闪闪流动,毫无忌惮地盯着柴荣,道,”陛下可曾记得,臣妾说过,即便此生都不能爱上陛下,也一定会坦然相告,不会欺君、骗君。“
这番赤裸裸的表白,无异于当年在殿上宽衣。众人的鄙夷之声顿时响起,就连郭妃也不住摇头,捂了宗训的耳朵,似不忍听闻之状。解忧却惊得差点喷笑,这句话算是青楼的入门情话,对不谙情事的愣头青尤其有效。果然,柴荣闻言,眼光一敛,勾起了心中的柔肠,正欲出言安慰,却被符皇后断喝声打断:“恬不知耻,身为妃嫔,却心系他人。竟在大殿之上做这般言论,对妇德伦常可有半点敬畏之心?“
柴荣皱了皱眉头,眼神中满是无可奈何,对秦妃道,“无论你是不是贡女,如今身为皇妃,便要知道谨言慎行,不可不再任性胡说。“
秦妃凝视柴荣,淡淡笑道:“臣妾只是想告诉陛下,臣妾从未在您面前说谎,从前未有,将来也不会。至于臣妾所谓的故人,陛下从未问过,臣妾也未提及。今日被逼至此,臣妾便让大家见见这位故人。”说罢,秦妃顾不得他人狐疑的神色,微微挺直了身体,从腰间解下一个样式别致的香囊,打开外面的布包,露出一个大约婴童手掌大小的木匣子。将面上的木板推开一些,露出里面灰白色的灰烬,却不知是何物。
众人面面相觑间,霜贵人突然反应过来,像被蛇蛰了般跳开,满脸嫌恶的模样,恶狠狠地说:“这是死人的骨灰。”
秦妃淡淡一笑,道:“你倒也识得。”
此番变故倒在皇后预料之外,她迅速递了个眼色给霜贵人。霜贵人会意,走上前,唾了一口,道:“这等晦气之物,是宫中禁忌,偏你随身携带,光这一例便该活活打死。”
柴荣对霜贵人的恶言收紧了眉头,却又在下一刻缓缓松开,抑制不住激动道:“他死了?”
秦妃面有戚色,道:“臣妾并非生而为妃。两国大战前,臣妾亦不知会远离故土,远嫁此处。他是我自幼选定的未婚夫,为国出战而死。渡过长江之前,我将他的骨灰混上了故国的沙土,聊寄相思而已。“秦妃说罢,仰起头,目光盈盈含情,”臣妾答陛下所问,那人不是赵帅。”
她的话说得这般动情,在座各位不少是自远处嫁来女子,心中不由多生了几分戚戚之情。霜贵人冷哼一声,面作镇定道:“骨灰都拿出来了,真是膈应人。不过那日赵帅到你屋里之事,你又作何解释?”
一旁的兰玉闻言,慌忙磕头不止,赌咒发誓道:“奴婢亲眼所见,若有半句虚伪之言,死后愿落阿鼻地狱,不得超生。”
秦妃眼风淡淡扫过兰玉,像在打量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声音清泠有利,像在诉说一件事实,“赵帅从未到过昆玉殿。”
没想到她竟生硬地赖掉,兰玉不觉露出了三分慌张的神色,脱口道:“奴婢分明记得,赵帅是二月初九,到了昆玉殿,在前殿呆了半个多时辰,奴婢不会记错。”
秦妃只淡淡道:“你记错了。”
雅贵妃刚领了柴荣的训斥,此时却又忍不住“嗤”地笑了一声,道:“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便是争到天亮也没有个结果。不过臣妾想来,这兰玉是秦妃自己宫里的人,能站出来指证自己的主子,不论存了什么心思,也是拼尽了自己后半生的安逸日子,所言却细致入微,听着倒不像假话。”
兰玉连忙磕头称是,“奴婢确实句句属实。”
郭妃倒是不屑,道:“这兰玉充其量不过是在外间伺候的宫女,所谓亲眼所见的也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节。况且时过数月,便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赵帅就是那日乔装之人,这份本事,臣妾自问是没有的。”
柴荣凝视着秦妃一脸的坦然,他自然很满意她的答案,可是却不能尽信。柴荣略带歉意地将目光移向兰玉,询问道:“除了你,可还有别的人证或物证?”
兰玉紧咬牙关,并未作答。
锦柔在旁早已听得索然无味,见此僵局,不失时机地插嘴道:“闹了半天,原来只是一个宫女口说无凭的孤证。凭她这身份也配与秦妃对峙,这般不分尊卑即便在我党项,也不能如此草率。”
锦柔的话是个大道理,但对于宫妃私情的处理向来是不论常理的。历来只要有人检举,必得查究,即便查不出实证,这妃嫔一生的清白也毁了,后半生便在不死不活的过着。宫妃们皆知此理,平素对伺候的宫女大多和颜悦色,轻易不打罚。
霜贵人当然明白此中关节,她悠悠道:“郡主出身外邦,不明白此事的难处。两人私会密室,本就不易被人察觉,能有些许破绽露出,已是难得,如何能强求实证。“
这么一来,局面再次凝滞。柴荣半靠在宝座上,手指在眉间摩挲不已,半晌未开言。
“奴婢有物证。”兰玉突然一声,惊得众人心头同时一凛,目光紧紧盯住她身上。
兰玉重重地磕了个头,抬眼偷望了一眼符皇后,迟疑一刻,像是下定了决心般,抖抖索索地从外裙内解下一个翠绿色的玉牌,双手递给柴荣,瓮声道,“奴婢之所以能认得赵帅,是因为……因为事情发生后没几天,有人送了奴婢这个东西。说是黑衣军的信物,说奴婢对他们主帅有恩,可凭此物,到京中六尺桥头的一家典当铺中兑换白银千两。奴婢想到那日之事,心想这许是给奴婢的封口费,便收下了。这……也算是个铁证。”
柴荣接过玉牌,对着光仔细查看了一番,冷冷道:“那你怎麼没去兑换白银?”
兰玉咬着嘴唇,道:“去了,可……可六尺桥周边几里,都没有典当铺。奴婢……奴婢想,许是搞错了,才特意留心赵帅,方确定正是那日出现在昆玉殿的男人。”
柴荣的口气听不出半分情绪,“那你之前为何不将此物拿出?”
兰玉连连磕头,道:“此事奴婢未弄明白,不敢擅自回禀。若不是秦妃矢口否认,陛下紧紧相逼,奴婢也不敢将这私受贿赂之事讲出来。”兰玉见柴荣面色铁青,又转向符皇后,呼道,“皇后娘娘,奴婢说的都是实情,这也确是黑衣军送来的东西,上面有黑衣二字,奴婢找人问过的。”
符皇后气得面色铁青,她没想到遇到一个自作聪明的兰玉,为了贪图小利,竟隐瞒了如此重要的关节。她压了压心中的愤怒,神色恭谨道:“臣妾此前未曾听闻此事,还请陛下查验。”
柴荣冷笑了一声,命人将玉牌递至贺氏面前,道:“赵夫人便在场,可否替朕查验一番。”
贺氏支起病体,端然行了一礼,方才拿起那玉牌,细细查看,又恭恭敬敬地放下,欠身道:“陛下知晓,黑衣军从未有过玉牌之类的信物,此乃矫伪之物。”
兰玉大惊,连连磕头,“奴婢……奴婢不知,这确实是赵帅所赠之物。也许是……赵帅私藏,赵夫人不识得。”兰玉声若蚊吟,无力地反驳道。
“蠢货!”柴荣怒斥道,“玉石素有招灵的功效,黑衣军对玉石避之不及。即便有信物,也不可能用玉石制成。”
解忧微微颔首,黑衣军往来与新坟古墓之中,从来身边只带木器辟邪。玉石,一直都是军中禁品。以符皇后的心思,自然不至于犯下这般大谬,想来可能赠玉牌的人便是,秦妃。
秦妃依旧静静地跪在那里,想一支旁逸横出的清水芙蓉,在满殿娇狂诡异的气氛中,仿若与己无关的旁观者。那日赵匡胤贸然进宫后,她派人仔细查探了赵匡胤接触过的所有人,将所有知情者都灭了口,唯独留下一个兰玉,又假装以黑衣军的名义赠送了一块漏洞百出的玉牌。为的便是这一刻,将局面翻盘。
这个女人真沉得住气啊。解忧在心里暗自感叹。
柴荣缓缓转过身去,盯住符皇后,澹然道:“皇后要不要再验验真伪?”
符皇后面色微微发白,强自镇静道:“臣妾相信陛下公允。许是有人为混淆视听,故意将一块假玉牌送给了兰玉。”一百件真相中混进了一件假证,便足以让人对其它真相置疑。
“皇后这话太牵强了。”锦柔轻轻皱起了如远山含黛的峨眉,轻轻道,“究竟是以假为真,还是以真为假,如今已经很清楚了。必然是有人要嫁祸秦妃与赵帅,找来与赵帅相貌相似之人,故意在这个宫女那留下印象,又以玉牌引诱她却求证赵匡胤,没想到这块玉牌画蛇添足,反而成了证明阴谋的关键。“
兰玉磕头不已,慌忙道:“奴婢愚昧,受人蒙蔽,皇上恕罪,恕罪。”
郭妃轻轻笑道,“郡主确实好心,倒替这个奴才把罪责摘得干净了。臣妾在宫里时间久了,早见惯了这些奴婢趋炎附势、卖主求荣的丑态。为了些许利益,哪有她们不敢说的谎言。或许这事从头到尾都是她凭空捏造的,还弄了块假玉牌来欺蒙陛下。幸得陛下圣明,才未被蒙蔽,不让秦妃与赵帅蒙冤。“
雅贵妃见势头不对,忙见风使陀道:“郭妃这话不错,若由得此人在宫中兴风作浪,连自己主子都敢混乱攀咬,还有什么做不出的。请陛下早下决断。”
柴荣的目光静静一沉,眼中的疑虑显然并未完全消除,他转向贺氏,问道:“赵夫人以为如何?”
贺氏淡淡说道,“妾身一介女流,不敢妄议。只斗胆问一句,对赵帅的置疑与流言为何偏偏发生在此时?”
一句惊天,柴荣低垂的眼睑微微颤动,恳切道:“是朕约束不力,容得这宫妇在此生事。“柴荣转身指着兰玉,杀气凛然道,”这贱人中伤主上,赐殿前杖毙。“
兰玉吓得面如土色,与拖她的侍卫挣扎抗争着,极力喊道:“奴婢没有说谎!都是实话!娘娘,娘娘救我。”
符皇后冷峻着脸,牙齿在下唇咬出了深深的痕迹。她目睹着优势在眼前转瞬即逝,她算到秦妃的巧舌如簧,却没料到自己选中的棋子竟如此愚笨。本就是刀尖上的角力,一招失措,时机已过,便再难追回。
解忧扶着贺氏,遥遥地站着,见那兰玉被衣冠不整地拖出去,听她的呼号之声在耳边越来越淡,终于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贺氏的身体颤抖得厉害,解忧自己也近乎脱力,两人相互倚力,像两张无所依靠的浮萍,随波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