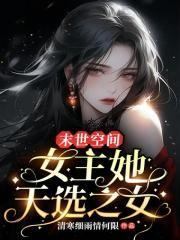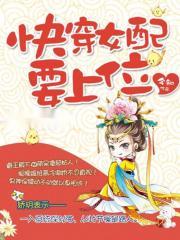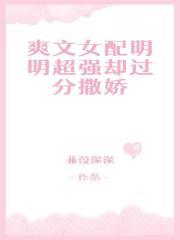大众文学>双生夫君 > 第838章(第1页)
第838章(第1页)
整幅画潦草,就剩这颗绣球和陆杨精细刻画,成了画面的中心。
状元郎随风飘飞的大袖子上写着一串小字:带净之到此一游。
最严肃的地方,就是金殿之上。
谢岩画了两幅小画。一幅是他殿试时,小小的陆杨趴在他的答卷上,侧目对人,充当镇纸。稍一分心,就会对上眼。
一幅是被点为状元时,陆杨在他帽侧的簪花里探头。像一只花中精灵。
事实上,上殿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佩戴簪花。
陆杨喜欢小人镇纸,想要个状元郎的样子。
谢岩答应给他弄一个。
陆杨又看画,指着骑马游街那幅画问他:“你不是说那天不高兴吗?”
实话最让人动心。
谢岩说:“你不在,我只觉得吵。”
所以那么热闹的场面,只是一些波浪线,像是热浪,要将人淹没。
陆杨再看画,就懂了他为什么会有个绣球了。
热浪会把人扑到地底,但球体会随之起伏,送他去谢岩那里。
时隔很久,陆杨又用了往日的夸人方式。
“阿岩,你哪天不读书了,去画画也是能挣大钱的。”
谢岩要点实在的。他凑过去,侧着脸等陆杨亲。
陆杨推推他的脸,没一会儿又笑,把他揽过来亲嘴。
提到画,谢岩这阵子在家,除了陪陆杨,就在跟字画打交道。
他考乡试时答应的两幅画已经装裱好,还有一幅是全家福,正在画。
装裱好的画,交给他娘了。
赵佩兰拿着两幅画卷,去隔壁屋找陈桂枝。
她俩在堂屋就把画卷打开看。一幅是陈桂枝的单人画像,少了些生活感,多了些端庄仪态,是坐在交椅上的样子。
这是一幅标准的肖像画,她坐姿端正,目视前方,唇角微微含笑。这样的画很容易画得呆板无神,陈桂枝最突出的性格需要动起来才好展示出来,但在这幅画里,她的泼辣略微内敛,有点不怒自威的味道。
赵佩兰跟她说:“大户人家的老人都叫‘老太君’,下面儿孙成群,都指着她教养。你以后就该是这样的。”
陈桂枝找陆柳拿了小铜镜,对着脸照照,又看看画上的人样,笑得合不拢嘴。
“你家儿子好本事,这是怎么画的?怎么看起来像我又不像我的?”
模样神态都是她,却比她端庄威仪。
赵佩兰也是说大实话,“这就是照着你的样子画的,你要不长这个样子,他还画不出来!”
哎呀!陈桂枝都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了。
她们再展开另一幅画卷,这是她们俩的画。两个女人静立画中,背景是模糊的街巷,是两人说笑的神态。
两人有一阵没说话,再看已是泪眼相对。
赵佩兰抓着她的手,说:“哎,老姐姐,真是舍不得,哪天你家大峰到京城来,你一定要跟来。我好好招待你!”
陈桂枝答应了,“不远了,不远了,京城也不远,我俩都有福气,孩子们有出息,还能到京城见见世面!”
这两幅画,她们一起选地方挂起来。
陆二保和王丰年从街上回来,大包小包的去看陆杨。
来府城以后,他们手上一日比一日阔绰,要买什么不用抠搜的算着省着。
他们怕陆杨难拿行李,又怕给了银子,心意不到位。犹豫再三还是买了东西。
这阵子能吃吃、用用。以后年年都有信件往来,他们再做些衣裳鞋袜捎带过去。
才过去一年,他们也有了成长变化。
人到中年,再谈成长,他俩都挺不自在的。但确实,走出村里,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去尝试了另一种可能,他们的心比以往豁达。
去年的他们,想要留在村里,相依孤老,不拖累孩子,也不让孩子为难。
今年的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想要留在府城,不再去更远的地方。理由却不是拖累、为难,而是他们适合这里。
他们能把话说开了。他们是内向性子,话也不多,留在府城,都常要两个孩子上门支应,跟他们说话。去了京城,他们又要重新适应。
陆杨可能会为了他们再开个小食铺,让他们有事做,不憋闷。他们觉着不用。他们喜欢三水巷。
他们相信,今年的陆杨,也不会认为这种选择是厚此薄彼,是留一个弃一个。
他们说:“哪天你们得空了,回来瞧瞧。我们就在这里。哪天柳哥儿出息了,我们也出去见识见识,去看看你。”
陆杨看着他们,笑得坦荡。
“哎呀,又不是什么大事,看把你们紧张的,脑门都是汗。人往高处走嘛,以前从县里到府城,现在从府城去京里,我们先去探探路,以后你们来了就好安家。就像来府城时一样,不用这么难过,都会再见的。”
再坦荡也要面对别离。三水巷的人家,逐一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