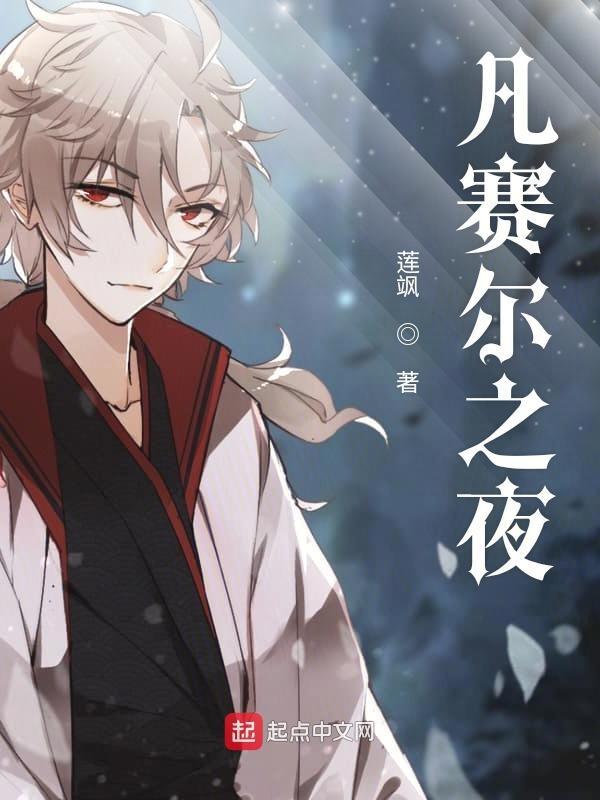大众文学>汴京觅食记沈 > 第93章(第1页)
第93章(第1页)
沈渺得意地挑挑眉:“阿姊刚接了个大生意,过几日要去辟雍书院的冯博士家做席面,能挣这个数。”她把两只手都伸了出来,在济哥儿面前晃了晃。
沈济惊喜道:“十贯?”
“狭隘了吧,再猜,往大了猜。”沈渺喜滋滋。
“二十贯?”沈济有点儿不敢往上猜了。
“是十两。”沈渺搂住他的膀子,悄悄在他耳边说,“金。”
沈济瞪圆了眼,甚至都不敢吐出那个字,嘴唇动了动,只冒出来一口气:“金?”
“金。”沈渺愈发沉醉,她这辈子都还未见过金子长啥样呢!上辈子她也最喜欢金了,但她不买首饰,而是每年到银行里买些金块,再把家里的保险柜塞得满满的,每年坐在那数一数,她便会觉着好生幸福。
沈济也被震得身子摇晃了一下。
“好了,咱们偷着乐就成了,万不要说出去啊。”沈渺把手往嘴上一捏,“你去叫湘姐儿起来了,给她洗洗脸,换身衣裳,阿姊再做一锅爊肉,咱们便出发。”
卤汤现成有,便只要将这些肉剁开洗净焯水后放进去便成了。刚将肉下锅,正要去搬门板关门,忽然跑进来个眼熟的小厢军,一进门便急切地嚷道:“沈娘子,你这时辰便要关门了吗?幸好我来得巧,快,包二十份速食汤饼来。”
沈渺认得他,起先便是他领着厢军教头一大帮人进来吃方便面,还吓了她一跳的。后来他也常来吃面,不过后来有空闲慢慢坐着吃,便都点的是羊肉面,唯独忙碌时才会包几份方便面回去吃。
“好嘞,就来,怎么今儿要这么多?”沈渺随口寒暄,进去飞快地包好,用麻绳捆成一串出来,递给他,“这些日子也许久没见军爷们来光顾了,可是有什么大事儿忙得紧?”
“快别提了,秦州正平西羌之乱,便生了些流民,有些都流窜到蔡州城外了。教头谨慎,怕届时有不法之徒混进城来,生出乱子便不好了。因此如今日日都派人四下巡守,夜里也不让归家,说是以备不时之需。”小厢军打着哈欠,显然这段日子缺觉得厉害,又眨眨眼笑道,“值夜时肚子饿,又不想啃饼子,还是沈娘子这儿的汤饼好,热乎乎吃下去人也精神了。”
沈渺担忧道:“秦州的乱子那么大吗?”
“听闻郗老将军已经收复那些贼子抢去的两个县了,想来有惊无险,很快便能平息了。”小厢军摆摆手,“不必慌乱,流民是进不来汴京城的。咱们守了几日,也只抓住几个浑水摸鱼的蟊贼。”
沈渺面上不显,送走那厢军后却还是决定一会儿推自家小摊车出门,多囤些不易坏的粮食得好。省得粮价大幅上涨,她的汤饼铺子也无以为继。
正琢磨,湘姐儿打着哈欠走进灶房里,揉着眼说:“阿姊,我不去书局了,我要去找狗儿玩。”
她还惦记着狗儿昨天挨了打骂,哭得那样惨,今儿便想瞧瞧他如何了。
沈渺想了想:“成,那你和有余在家吧,雷霆也留下来,阿姊买了东西就回来。你和狗儿玩够了,若是阿姊还没回来,便去顾婶娘家里等,阿姊会去与顾婶娘说一声,叫她帮着看顾你。你与狗儿即便要玩也在巷子里玩,可不许跑到街上,知道么?”
湘姐儿脆生生道:“知道啦,我不会乱跑的。”
说完她便拉着有余往李家的后院门跑。李婶娘午睡还没醒,李家静悄悄的。沈渺探出头去看,只见湘姐儿在李家门口学狗叫,没一会儿李狗儿便顶着个肿眼泡探出了脑袋,两人在门边说了两句悄悄话,他便蹑手蹑脚地溜出来了,两人拉着有余一溜烟跑到水房背后的排水渠里躲着说话去了。
这几日没下雨,排水渠弯弯曲曲,还是干涸的,巷子里的孩子都喜欢钻进去玩捉迷藏。
沈渺又去顾家说了声,顾婶娘便搬着板凳到门口来,一边摘菜一边远远看着,摆摆手:“你去忙吧,我在这儿坐着,他们怎么也出不去巷子的。”
于是沈渺很快收拾好,把铺子关上,小摊车上的大伞与底下的碳炉都取下来,便与济哥儿一块推着走了。虽说内城里有不少近一些的书局,但沈渺宁愿绕远路去周掌柜那儿买,一是照顾周掌柜生意;二是他的书局离辟雍书院近些,不少书院的学子与他往来,他知晓不少书院里的事儿,沈渺正好能为济哥儿打听打听;三是方便面作坊与做席面这两桩生意都是意外之喜,今儿谈妥了她心情激荡高兴,可是财不露白,她没法逮着人说,便很想出来走一走,将这份喜悦交给外头的微风与阳光去平息。
等走到兰心书局,沈渺基本也恢复了平静,撩开书局门口半卷的苇帘时,她心里也有些自嘲地想,她终究还是个为己悲也为己喜的俗人,不过当个俗人也挺好,她拥有的这些满是铜臭的庸俗回忆,能令她内心丰盈且快乐着。
甩掉那些胡思乱想,她进门时扬着声音,一边唤着:“周掌柜。”一边进去了。
一进去,她对上好几双眼睛,这才发现往日冷清的书局里难得的热闹,里头或坐或站,在柜台前围了好几个宽袍大袖的学子。
她的声音落下,便引得他们都回过头来瞧。其中一个娃娃脸的学子,立刻惊喜大叫:“沈娘子!”
“沈娘子也来买书?这段日子我被我阿爹关在家里,都没去铺子里吃汤饼,真是饿得都瘦了!”他扔下手里的书,自顾自地开始唠叨个没完,还激动地想挤过同窗上前来与沈渺攀谈,却又被身边的尚岸眼疾手快地拽了回去,于是扭头又不满地对友人嚷嚷道,“尚兄你拽我作甚,你不知,我被我爹关在家中,写了三篇颂汤饼的文章,颂的便是沈记的汤饼!你撒开,你理会不了,沈娘子是我等饕客的知音,是暗夜之明灯,更是孤舟之港湾……”
“宁大,快别念你那些酸溜溜的文了……”尚岸听得直打哆嗦。
“……”沈渺也抖了抖浑身的鸡皮疙瘩。
她想起来了,此人先前想买蛋黄酥给她拒过一回,后来方便面风靡之时,他串联了好些国子监内舍生与辟雍书院的学子漏夜翻墙出来吃方便面,结果还被姚博士撞个正着,后来便好些日子没瞧见他了。
看来是逃学吃面之事东窗事发,被家里关了禁闭,今日才得以解禁吧。
沈济将家里的车在门口支好后,便也钻进了铺子里。他默默地站到沈渺身后,眼神有些警惕地瞄了那激动得奇奇怪怪的“宁大”一眼。
这时,周掌柜掀开后堂的帘子走出来,一边侧身与身后高高瘦瘦的人说着什么,一边迈过门槛:“谢家九哥儿,你回书院读书要沙土作甚?我倒是有些河沙,原是用来养鳖的,便均给你一盆吧!”
说着二人回过头来,见到沈渺具是一愣,之后异口同声问道:“沈娘子怎来了?”
沈渺先跟周掌柜见了礼,再抬起头来,才发现周掌柜身后的是谢祁。
谢祁那腿终于好全了,先前虽早已拆了木板,但走起路来还有些疼,如今算是走路跑跳都没问题了,家里便催他回书院读书,他今儿也是来兰心书局买些笔墨,顺带再添补些其他用具,便要回书院去的。
沈渺见了谢祁总是没理由不高兴的,她上前轻轻一福:“昨日刚在夜市遇见九哥儿了,今儿又在这里遇见了。对了,还没告诉九哥儿呢,济哥儿考上了!考了第六呢!”
她顺带将济哥儿拉上前来,仰起脸,发自肺腑地感激道,“当初若无九哥儿出言提点,又借了济哥儿书册,他想来考学不能这般顺利,日后济哥儿在辟雍书院,也托九哥儿得空看顾一二了。”
“不必总言谢了,我的书只是锦上添花,这一切都是济哥儿苦心读书才得来的,当谢他自个才是。”谢祁没有居功,反倒笑着摇摇头,又转过头对沈济道,“恭喜,日后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学舍,也算半个同窗了,回头你入了学,我领你四下逛一逛。”
“多谢九哥儿。”沈济有些脸红了。
尚岸忍不住瞥了格外温和的谢祁一眼,心想,谢九何时对旁人这般热络了?还借书?还逛一逛?
宁奕却又凑上前来,垫脚勾住谢祁的膀子,小声而神秘地对沈渺姐弟二人道:“你们不知道吧?谢九可是我们书院里所有讲学博士的心肝宝贝,他当年考童子试是头名考入的,之后在辟雍书院,甭管什么考试,他亦从未做过第二的位置。他读的书、做的书批旁人不知,惟有我最是知晓,那写得极为鞭辟入里,又贴切精辟。嘿嘿,我每次旬考、季考、岁考总借谢九的书看,临时读一读,之后便每回都能取中,不至于被踢出甲舍。你家兄弟啊,当初能借到他的书,也算是捡到宝咯。”
沈渺惊讶地看了眼谢祁,原来九哥儿读书这般厉害?他平日里从不提,也不会在她面前炫耀自己的学识,更不会摆出高谈阔论的样子来,她便也从未曾想过他能厉害成这样。
谢祁被她一双透亮乌黑的眼瞧着脸颊发热,很有些不自在地转开眼去,轻声道:“沈娘子别信他的,他说话总是夸大的多,我读书谈不上多有天资,只不过比旁人勤勉些罢了。”
沈济却是读过谢祁写在旧书里空白处每一句每一行的批注的,他便也知晓那宁奕说得不错,默默点头。谢家九哥儿厉害之处不在于文辞多么华丽繁复,而是文字如刀,总能切中要害,他当初答题时,也下意识学他如此解题,想来这便是他能考中的关键了。
“不论如何,人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恩,日后九哥儿有什么需要我相帮的,一定直言。只要我沈渺能做到的,绝不会推三阻四。”沈渺坚持道。
谢祁心头鼓动,沈娘子眼眸认真,可她说了这许多,他都没入心,两只耳朵像是刮过一阵风,他只听见风中传来“沈渺”二字,下意识便问:“沈娘子的名字……是哪个字?是妙手谁烘染的妙,还是云帆淼淼巴陵渡的淼……”
他头脑发热,问完了,才知晓自个竟然在这儿恬不知耻地打听沈娘子的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