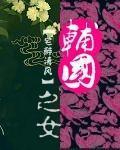大众文学>汴京觅食记沈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她手里还是紧紧地牵着那个憨傻的女孩儿,那女孩儿也亦步亦趋地跟着她的母亲,像一只离了巢便容易受惊的小鸟。
老妇人似乎也习惯了旁人异样的眼光,进来后并不在乎沈渺忽然的沉默,但也没贸然坐下,先是张望了一圈店里的陈设,又低头端详了一会儿脚下洁净的地砖与桌椅。再抬起头时,她有些茫然地望着墙上的食单。这个铺子好奇怪,没有殷勤地上来报菜名的小二,还贴了这样的食单。
难不成来她铺子的都是读书人?妇人有些后悔走进来了,她方才是看这铺子的匾额陈旧,门脸也小,便思忖着或许不会太昂贵才进来的。
但都已来了……她实在不识字,一点儿也看不懂墙上的食单,于是只能有些犹疑地问:“店家娘子……你…你这儿可有卖那等四文钱一碗的素汤饼?我只要一碗就好,多…多些面汤也无妨。”
沈渺回过神来,收起目光,端了两碗水放在他们面前,笑道:“有,你们坐着先喝点水,马上来。”
老妇人闻言松了口气,牵着她的女儿找了个最角落、最不起眼的位置坐下了。坐下后也没个闲,先从将帕子掖在女孩儿的领口,还帮她卷起了两只袖口,那女孩儿任由母亲照顾,时不时傻呵呵地冲母亲一笑。
那老妇人便又轻柔地抬起手,爱怜地给她别过碎发。
或许是因女儿不大会说话,她便也习惯了不说话,之后母子二人安静地等候着。
沈渺店里有素面,但她的素面全靠汤底儿,是仿照江南的阳春面做的,成本其实不算很低。
为何发源于高邮、扬州、上海等地的一碗素光面能得“阳春”之名?其实便是因为以往江南地区将十月称为小阳春,渐渐便有了“十”为阳春的隐喻,故而在扬州等地,阳春面一碗售钱十文,故而得名。
所以沈渺店里的猪骨清汤面也定价十文。尤其她用来做面的麦粉都是用粗面重新筛过的,用的肉也好,因此值得上这个价。
何况……别说富饶的江南,这四文钱的面,在汴京城里一样找不着。或许靠近城郊的脚店里才有。
她们难不成是外乡人进城来的?沈渺一边在心里猜测,一边偷偷用余光打量她们。
那老妇人从身边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瓷瓶,从里头倒了几颗小小的药丸出来,就着沈渺端来的水,仰头服用下去。
自个吃完了药,又在布包里翻出另一个药瓶,倒出几颗药来放在手心里,转过头耐起性子哄着那女孩儿吃:“有余啊,你乖乖吃了药,阿娘给你卖糖糕吃,成吗?”
女孩儿却仿佛见了什么洪水猛兽,一个劲地摇头:“不……不……”
“你吃药,阿娘再领你去敲两块饧糖可好?可还记得?那个总是叮当当、叮当当的糖。”
女孩儿这才犹豫了,勉为其难地吞了下去。那张有些独特的面孔皱成了一团。
沈渺悄然收回了视线,用筷子捞起锅里已经煮熟的两份面条和几片白菘,热气蕴藉之间,又转身从熬制的猪骨高汤里舀了一勺汤出来做这素面的汤底,最后在面上铺上白菘、额外加了一勺酱肉面哨子,再撒上葱花、点上几滴葱油,这简单而香的清汤面便大功告成了。
之后,她从橱柜里多拿了一只碗来。
她将实际是两份的面都装进一个大海碗里,笑吟吟地端了出来:“久等啦,面好了。这面刚出锅的,很烫,给您多拿一个碗,您可以分出来吃。”
老妇人却望着这满满一大海碗的面一下慌了神,急忙拉住转身要走的沈渺:“哎呦,店家娘子,你怎么做了这么多?我方才与你说了只要一碗素面,不要别的。你怎么还加了肉?我……我们母女俩本就是进城来找活儿干的,吃喝嚼用不得不紧省,实在没带那么多银钱……”
沈渺只好笑着解释道:“不是强买强卖,您放心吃。您来巧了,我今儿是头一日开业,您啊,又是这大中午头一个进来吃汤饼的。我家里有个规矩,头一位客人,要给您打对折,您放心,这些哪怕加了肉也只收您四文钱。”
那老妇人将信将疑地坐了下去:“果真?”
“果真。”
沈渺把袖子从她筋节毕露的手里抽了出来,指了指灶房:“慢用,我先进去忙了。”
“嗳……嗳……”老妇人有些局促地坐了下来,怔忪的目光重新落在眼前的大碗上,半晌,才颤巍巍拾起筷子,先给自己那傻闺女分了一大半,还将碗里的肉仔细地挑出来,全放进了她的面碗里。
沈渺进了灶房收拾案板、刷锅,其实却还是忍不住悄悄去看她们。
那女孩儿不怎么会用筷子,老妇人便用勺子一点点将面条压断,让她能用勺子扒拉进嘴里。看女儿吃得香,她这才开始吃那碗里剩下大部分是面汤的面。
沈渺便看着她吃下一口似乎愣了一下,渐渐地吃面的动作便变得狼吞苦咽起来,最后忍不住将面汤也喝了个干净。
她微微一笑,便又低头揉面。
这时候没有产检,更不知糖宝的观念,这些特殊的孩子降生到世上,并不是身为母亲的错。而且……他们或许会因为病情严重,便会因先天聋哑、智力障碍、心脏病、消化道畸形等病症不出几年便去世了。即便侥幸活下来,只怕也会被宗族、长辈遗弃甚至掐死,所以在古代,哪怕是这个富裕的大宋,普通平民百姓人家,也是极少能见到一些特殊的孩子,莫说长大成人,更莫说是个长大成人的女孩儿。
在这样重男轻女的时代,这位老妇人的女儿,竟然被她养得这么大了。
她并不知晓自己会生下痴傻的孩子,后来知晓了,也没有将她遗弃,而且咬着牙拉扯她长大。沈渺都不知要如何想象,她究竟耗费了多少心血、抵御了多少外人乃至亲人的刀枪剑戟,才能在这样的世道将她奇迹般养大。
一碗面,是她对这份母爱的敬意。
另外她也另有一点心思,想等她们好好的、安生地吃一顿饭以后再细细问一下。但她们一吃完,便好似生怕沈渺反悔或是多要钱一般,忙不迭离开了。
“店家娘子,多谢你了,这钱放桌上了。”
沈渺闻声探出头来,老妇人已经拉着女儿急匆匆跑出店去了,她忙从灶房绕出来,还冲她们的背影叫了声“哎等等”,她们反倒撒腿跑得更快了,一眨眼便消失在了街角。
她只能无奈地回去。
角落里那张桌上,整齐地放着两只吃得一滴不剩的面碗,以及被摩挲得发亮的四枚通宝。
之后铺子里便再没人上门了,如沈渺意料的那般,这时的午食还不算正经一餐,放弃午睡出来觅食的人总归是少的,不少店家干脆上了半边门板,直接回屋歇息去了。
里外静悄悄,沈渺又干完了活,百般无聊地撑着下巴,日头透过窗棂,一格一格地照在她身上,太暖和了,她便也趴在灶房里的条案上打瞌睡。
不知是不是看到了那对母女的缘故,她梦里似乎也回到了上辈子的幼时,她踩在板凳上偷摸着煎爷爷新买回来的带鱼,她从小学厨就此别人快一大截,偷吃的时候,都是她主厨,几个堂兄弟姊妹围在灶台边举着筷子等。
阳光是橘色的,因此这陈旧的梦境里也全被染上了橘色,最后她们几人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吃光了好几条带鱼,咸得满屋子找水喝,被爷爷奶奶有一个算一个臭骂了一顿,但他们这几个熊孩子相互看了一眼,挨了骂还哈哈大笑。
直到日头渐渐西斜,她才被指节轻轻扣在半墙柜台上的“笃笃”声吵醒。
醒来时她都还有些分不清梦与现实,毕竟她真的很久没有再梦见上辈子的事了。
带着脸上压出的几道歪歪扭扭的红印子,沈渺无知无觉地拢了拢松垮的发髻,迈着有些迷蒙的脚步,撩开了半片帘子。
没想到来客似乎正想探头看看里头有没有人,因此沈渺一撩开帘子,便对上了一双清冽透亮的眼睛,吓得她与来人都猛地往后一仰,双双拉开了距离,这才看清是谁。
眼前,是头戴儒巾,身着对襟直领大袖,淡雅朴素风姿翩然……但拄着拐的谢祁。
视线再往下一点,是两只手扒拉着柜台,仰着脸笑的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