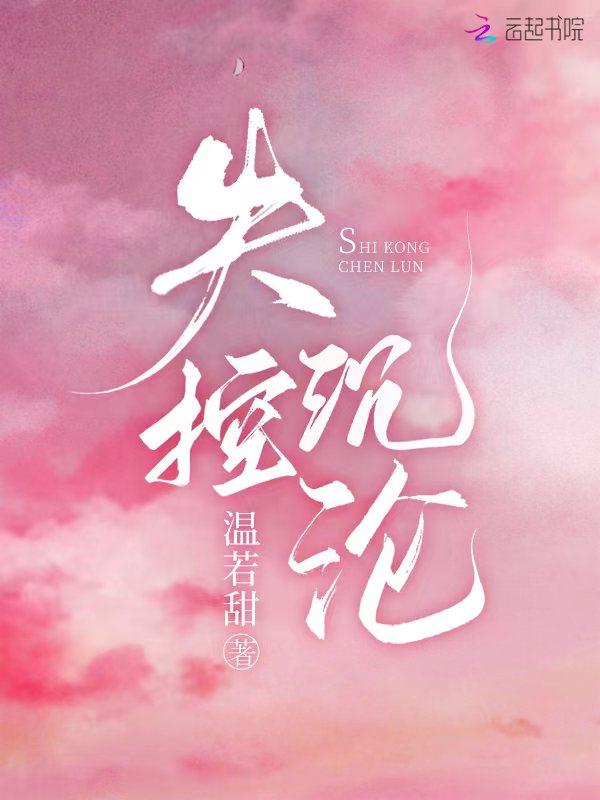大众文学>万历起居注在线阅读 > 第0042章 名场面沈念的训诫课上(第1页)
第0042章 名场面沈念的训诫课上(第1页)
翌日午后。
京师东北角,崇教坊,国子监。
众博士、典簿、助教、学正、学录、典膳(统称教习)与近千名监生齐聚于前庭。
乌泱乌泱,挨肩擦背,几乎站满了每个角落。
此刻,教习与监生们都是一脸懵。
国子监司业周子义只通知所有教习与监生午后在前院集合,但并未言明事由。
依照常例。
此等规模不是皇帝或阁老来训话,便是礼部有重大活动安排。
但这种事宜一般都会提前告知,甚至有文书传达。
而今什么都没有,祭酒与司业今日一直都未出现,略显蹊跷。
……
片刻后。
国子监祭酒王锡爵与司业周子义来到了前庭。
二人身后跟着数名仆役,还搬着一个高约三尺、直径约五尺的圆形木台。
王锡爵走到前庭中间,令仆役将木台置于中间,而后高声道:“绳愆厅监丞何在?”
两名监丞迅走出。
“以此木台为中心,教习围于前,监生围于后,迅排列成队,三位阁老很快便将到来!”
二监丞不敢怠慢,迅整起队列来。
教习与监生们一听三位阁老亲至,表情也都变得严肃起来。
他们虽爱讥爱辩爱高谈阔论,但在上官面前却怂的很。
礼数上不敢有丝毫差错。
不同于宋朝将国子监生当成香饽饽,明朝最喜欢整治的就是国子监。
特别是明太祖老朱开国时期。
洪武元年,国子监还叫做国子学。
第一任祭酒许存仁遭弹劾,死于狱中;第二任祭酒梁贞,罪归故里;第三任祭酒魏观外放后被杀;第四任祭酒乐韶凤,因病被免;第五任祭酒李敬,以罪罢免。
而在洪武十五年后。
国子学改名国子监,国子监祭酒更是屡屡被惩,鲜有善终。
直到老朱去世,国子监的日子才稍微好过一些。
朝廷之所以针对国子监。
是因国子监乃天下官学之表率,然学官们爱议朝政,胡说乱写,时不时还裹挟于一些党派门户之中。
整治了他们。
民间的书生文人便会收敛一些,朝堂上也会肃静一些。
但因监生是一批一批的。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总会有一小撮血气方刚、为清直之名不惧死但又眼高手低的。
故而,时不时就要整顿一番。
王锡爵与周子义之所以没有告知他们今日之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