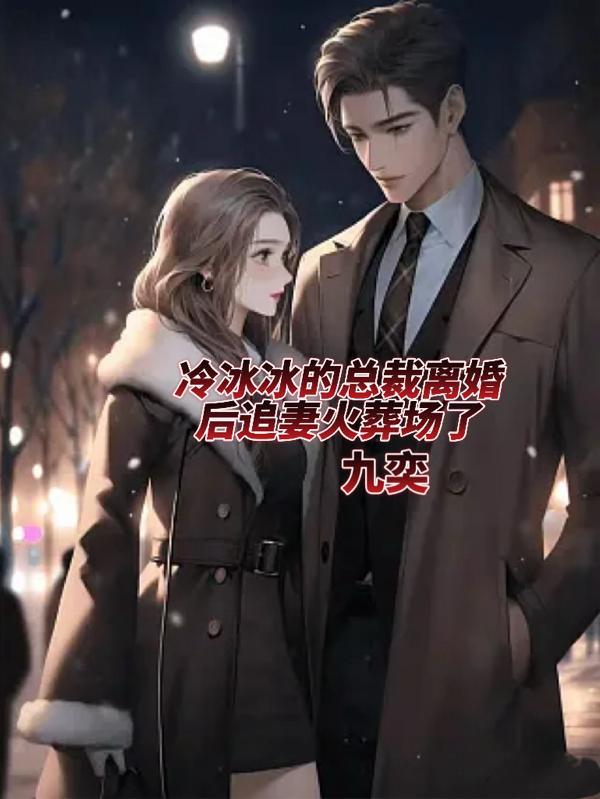大众文学>猫是人间的龙by画眉郎 > 第102章(第1页)
第102章(第1页)
仪式尚未正式开始,场地中央不时有工作人员来回走动,调整设备。前来参加的多半是普通市民,有拄着拐杖的白发老人,有蹒跚学步的幼童,有戴着头盔的骑手,有提早下班的白领,有相拥着不舍分离的情侣,有背着画板形单影只的学生……
有许许多多、好久不见的城市剪影。
不少人被冻得耳鼻发红,只能通过跺脚取暖。
但没有人提前离开。
他们守在风雪中。雪花落下,亲吻五彩缤纷的伞面,啪啪作响。
有一群四五岁的幼童在人群中穿梭,嬉笑打闹,为谁来扮演拿棉签的“大白”而争论不休,还有几个更大的孩子追在后头吵着要给前头的几人量体温。
嬉闹声中,响起一道脆生生的童声。
“妈妈,为什么说以后大家都不能戴口罩了呀?”
不少人下意识地循声望去,只见是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约莫三岁大的女童。女童独自举着一把小小的圆形瓜皮小伞,绿油油的,俏皮可爱,逗得众人不由发出善意的笑声。
年轻母亲略带歉意地朝周围人笑笑,好像在为女儿稚气的发言感到无奈。
“宝宝,”母亲轻拍女儿,声音柔缓,“在你出生之前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所有人都不需要戴口罩,不需要被棉签捅,不用量体温,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所有小朋友都可以去幼儿园,交朋友、学习、郊游。你以后也可以这样,这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小女孩仍旧懵懂,怔楞着,瞪圆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努力消化母亲的话。
她还太小了。这样小的孩子,出生在疫病爆发之后,是媒体口中所谓的“口罩后”宝宝。自他们出生起,从未见识过不曾被疫病污染的正常社会,在他们有限的人生阅历中,也很难理解可以随意出门玩耍的生活模式。
他们还想象不到,房子外头有一个无限广阔、不被约束的世界,那才应是他们的此后人生。
他们以一种非常态的姿势进入人生的社交敏感期,却极少有机会能无所顾忌地与同龄人交往。
他们甚至很少真正意义上地毫无顾忌地拥抱过一位朋友。
半响后,小女孩喃喃问道:“妈妈,我真的可以摘下口罩吗?”
“当然啦。”
于是,得到允许的小女孩不等妈妈帮忙,懂事地自己动手,轻轻扯下小小的口罩,珍而重之地抚平口罩的褶皱。她没有乱扔,只是用手指紧紧捏着口罩一角,嘴角抿起,面露紧张,就像眼前面对的是未名的巨兽。
大人们也沉默下来,陷入沉思。
他们想起和高中时代无异的大学时光,想起自己还未做好准备就要被强行推入社会的恐慌,想起无疾而终的创业计划,想起不得已断掉的供房贷款,想起远在家乡多年未见的亲友,想起不愿再想起的痛彻心扉……
三年,不长,却也足够长。
是谁无情地偷走了他们人生中的三年光阴呢?
而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那个平平无奇的日子,当人们收到疫病清除通知的那一天。他们惊喜却也恐慌。他们不敢出门,一遍又一遍地刷着辟谣信息,想等新闻,又害怕等到新闻。
紧接着,更多的媒体跟进报道,头条热度保持了半月左右。也正是在这短短两周内,各地病例火速清零,再无新增感染者。
病毒同它来时一般,离开得悄无声息。
像是一场奇迹,又像是一场诡异荒诞的梦。
时代落下一个强有力的休止符,暂停键重启,社会的心脏重新跳动,就像它曾经历过的许多次重创那样,起初很缓慢、却也坚强地愈跳愈强壮。
扑通——
扑通——
扑通——
有龙入梦来
活动尚未完全开始,庆典的氛围却越炒越热,人群也越聚越多。哪怕没有多少人开口说话,沉默带来的压迫感也不经意为所有参与者的心染上几分激动和期待。
只是这样的静默只维持了不过一刻钟,活动迟迟不开,人们的神色逐渐由平静变得浮躁,不少人开始同身边人交头接耳起来。
“我都好几天没戴口罩了,怎么现在才来摘口罩?还搞个活动,有什么说法?”
“现在年轻人不都讲究那个什么……仪式感嘛。我女儿之前还和我说他们学校也搞过类似的活动,说什么现在的学生毕业都不流行撕书了,要撕口罩撕‘绿码’。”
“据说就是大学生搞出来的。”
“大学生?毛春有啥大学?”
“你没听说啊,理工学院在毛春开了分校,已经建成了,冬季小学期马上就开学。”
“理工学院?哟,那可是知名大学,了不得。”
“我以前就想鼓励我女儿上理工学院,这个愿望在她上初中之后我就再也不提了哈哈哈哈!”
“开学了就热闹了吧?难怪最近好像开了不少店,都是年轻人爱逛的。这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了哦。”
“都这么多年了,瘟神总算走了。过两天冬至,我们家就得去祭祖、送瘟神、除晦气。”
“今晚不就有烟花吗?好几年不许多放了,今年春节估计得破例。你们知道吧,烟花爆竹就能除疫送瘟神。想想就热闹啊!”
瘟神么?
小黑猫陡然振奋精神,竖起两只尖尖的小耳朵。
这不是小黑猫第一次在人类的对谈中捕捉到疫病一类的关键词。疾疫时有发生,不算多稀奇。只是综合这些人类所言,一场时疫竟持续数年之久,灾被全国乃至更广,实属罕见。
小黑猫心念一动,下意识抬起爪子就要起卦。卦象未成,他幡然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