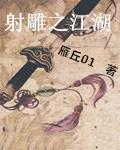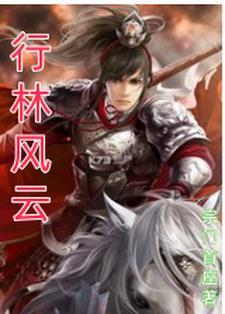大众文学>穿越成了武 > 第231章(第1页)
第231章(第1页)
但是现在不一样,刘彻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屡次兴兵对大汉以及大汉的百姓负担有多重,他之所以坚持,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大汉的江山不能稳固,这天下也不能安定。
但是他可以这么做,不代表他后代也能这么做,毕竟刘彻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平定了外族对大汉的侵扰之后,大汉反而重蹈了秦朝灭亡的覆辙。
所以刘据的宽厚仁慈,正是刘彻所需要的。
只是刘彻自己也没想到,刘据虽然宽厚仁慈,却不是只一味地宽厚仁慈,在对待西羌的问题上,他展露了自己强硬的一面。
刘彻饶有兴致地问刘据:“用武力镇压之后呢?”
听到刘彻这么问,刘据就知道自己刚刚的建议得到了他的认同,当下心情不由地振奋几分,他继续道:“儿臣刚刚看过捷报,李将军在上面说了在伉表兄和西羌大战一场后,他用攻心为上的策略,成功瓦解了西羌内部的联盟,成功迫使他们向我们大汉臣服。”
“可见西羌内部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拿起武器和我们大汉为敌的,所以我们可以采用怀柔政策,以利诱之,使得他们真心臣服和亲近我们大汉。”
听完刘据的话之后,刘彻笑了:“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对于刘彻而言,如果真的有办法让西羌真心臣服和亲近大汉的话那么当然是最好了,因为西羌各个部族的人基本生活在湟中(青海)地区,那里的海拔高,适合常年生活在那儿的羌人,但是并不适合常年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人。
因为一个高原反应就足够坑死他们了,所以卫伉在这次平定西羌一战中能够有如此亮眼的表现,而李息又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迫使西羌臣服,这都足以让刘彻感到惊喜了。
当然了,如果后续大汉能够顺利“治”服西羌的话那就更好了,否则一旦西羌再次叛乱,大汉又得派兵镇压的话,那就得耗时耗力,耗财耗兵了。
因为自家大兄此次带兵平定西羌,所以作为弟弟的卫不疑早早就已经把西羌的情况了解透了,见刘彻赞同刘据的建议,他出声道:“西羌是游牧民族,而湟中又地处高原,若是我们大汉派兵驻扎西羌的话,将士们的粮食要怎么解决?”
虽然卫不疑现在并不知道刘彻如果要派兵驻扎西羌的话,会派多少的士兵,但是粗略一算,少说也肯定有几千人的,多的话甚至上万人,这么多人驻扎在西羌的话,总不可能靠中原长期运输粮食给他们吧?
倒也不是给不起,而是如今大汉的运输能力有限,一两次还好,长此以往的话这对大汉而言肯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偏偏他们还不能不送,要不然驻扎在西羌的将士们得怎么办?
卫不疑说,“便是屯田只怕也解决不了驻军将士们的粮食问题。”
“到时候我们可以派人到西羌兴修水利,教羌人种植五谷,让他们发展畜牧。”小九说,“西羌地处湟中,跟我们中原相比肯定是较为落后的,但是羌人本就是游牧民族,善于畜牧,到时候让他们与中原互通有无,一来二往的,自然能够在他们和中原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用贸易手段制衡西羌部落。”
“其实羌人与汉人除了生活习惯不一样之外,大家都是普通人,大部分都希望能够过上安稳日子的,只要稳住大部分的羌人,那么即便他们内部仍然有野心不死的羌人,他们也如同苍蝇的翅膀一样,扇不起多大的风浪。”
在小九说完之后,张安世才接着道:“除此之外,为了防止西羌内部再次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将他们各分支打乱,再将部分羌人迁移到北地郡,让他们与汉人一块生活。”
羌人和汉人之间在此之前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所以张安世这么建议并不担心将部分羌人迁移到北地郡之后,会和当地的汉人发生无法调节的冲突和矛盾。
刘彻听完这些小辈们各自发表了自己的建议之后,突然发现大汉的未来是不必愁了,因为他们这帮才十几岁的孩子不仅能发现问题,而且还能解决问题。
“你们的建议都很不错。”至于细节当然是还需要再完善了,比如说派多少人去西羌驻军,又比如说派谁去兴修水利,教羌人种植五谷,以及将部分羌人迁至北地郡之后要如何安置他们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样,小九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很快地就把管理西羌的框架给搭起来了。
刘彻道,“到时候可以置护羌校尉,靠镇压、拉拢和分化的手段压制西羌诸部。”
这护羌校尉就和刘彻在元狩四年设置的护乌桓校尉差不多,不同的是当年刘彻设置护乌桓校尉的时候,目的是为了让乌桓从此不再和匈奴交通,而刘彻现在有意在西羌设置护羌校尉,目的当然是为了镇压西羌,预防他们的部落叛乱了。
刘彻看了卫青一眼,然后道,“卫伉此次平定西羌,立下大功,原本应该班师回朝,接受封赏才对的,只是西羌虽然平定了,但是后续的管理问题才刚刚开始,仲卿,我有意让卫伉继续留在西羌,配合李息解决西羌的管理问题。”
虽然刘彻没有明说,但是卫青也听得出来,卫伉要是继续留在西羌的话,那么少说也得在那儿待上个两三年,长的话说不定是五六年,甚至七八年。
毕竟管理西羌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想要让西羌如同东羌一样彻底地融入大汉,被中原同化,别说是刘彻这一代人了,说不定就连刘据那一代人都没办法做到。
一切都只能够靠持之以恒的坚持。
当然了,卫伉不至于得等到西羌彻底融入大汉,被中原同化之后才能够回长安,但是至少也得跟李息他们一块将刘彻下达的政策在西羌推广和实施起来,初见成效了才能回长安,否则的话只怕卫伉自己也不好意思回来了。
卫青从来不干涉刘彻的决定,这次也一样,他说:“陛下决定就好,臣没有异议。”
于是卫伉在西羌一待就从元鼎六年待到了元封四年,是的,刘彻又又又换年号了,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元封四年的秋天,卫伉终于带兵从西羌回来了。
抵达长安的时候,卫伉能够明显地感受到长安的变化,尤其是长安城内的地面,卫伉也不知道铺上了一层什么东西,只觉得它灰扑扑中带着一点黑,但是却意外的平坦和干净,卫伉用脚感受了一些,只觉得它十分的坚硬。
这样的地面不适合跑马,因为太硬,也太滑了,容易伤到马儿的蹄子,但是却很适合人在上面行走,他甚至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是下雨天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的话,肯定不会再发生像以前那样,身子没有被雨淋湿,靴子却沾了一脚泥的情况了。
卫伉很好奇:“这地面铺的是什么?”
“是水泥。”回答卫伉的是卫登,自从得知卫伉终于要回来长安之后,高兴的人有不少,但是最高兴的大概就是卫登了,天天掰着手指算日子,恨不得时间咻的一下就来到他大兄抵达长安的这一天。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了卫伉抵达长安的这一天,卫登要不是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儿了,他都恨不得猴到卫伉的身上,就跟小时候一样。
不过卫登虽然顾及着颜面,没有做什么失态的事情,但是一见到卫伉,他就直接“粘”在了他的左边——因为右边已经被小九占据了——见卫伉对水泥地好奇,他立马为他介绍道,“这是小九让人捣鼓出来的,陛下见好使,就让人给城内的大街小巷都铺了起来。”
听说这水泥能被捣鼓出来又和小九有关,卫伉忍不住转头看向自己右边的小姑娘……不对,应该是大姑娘了,卫伉笑道:“小九你的小脑瓜子怎么能那么好使呢?”
卫伉这么夸小九,倒也不仅仅只是因为水泥而已,也因为在他留在西羌的第一年,他就收到了小九让人给他送来的、一种名叫“芸薹”的种子。
除了种子之外,还有厚厚的一本教人如何种植芸薹、如何收割芸薹、以及如何食用芸薹和如何利用芸薹榨油的书。
卫伉并不知道芸薹是什么,但是得知芸薹能食用,而且还能够榨油之后,他立马感觉如获至宝。
虽然小九已经在信中说了,这些芸薹都是通过西域那边传入大汉的,在此之前大汉并没有人种植过芸薹,所以不确定卫伉如果让人种植芸薹的话能不能成功,但是基于对小九的信任,卫伉还是二话不说就带人照着小九教的办法开始种植芸薹了。
芸薹的种植方式并不难,而且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所以即便卫伉他们毫无经验,但是第一年他们仍然种活了芸薹,只是产量不太理想而已,但是卫伉没有气馁,带人继续种植。
通过总结经验和及时调整,如今西羌种植的芸薹产量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逐渐成为西羌百姓的收入来源之一了。
“没办法。”小九一本正经地道,“天生聪明难自弃。”
小九这话一出,别说是卫伉他们了,就连最小的霍嬗也忍不住笑了起来:“阿姊羞羞脸。”
历史上的霍嬗在十岁那年就夭折了,然而他现在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小少年了,不仅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好好的。
小九有理由怀疑是因为元鼎元年那一年霍嬗没有跟刘彻一块去泰山封禅所以才逃过一劫的,不过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也好,霍嬗能够避开他的死劫那都是一件好事。
这样她阿兄也不必年纪轻轻就经历丧子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