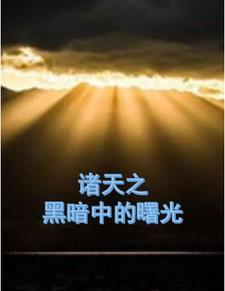大众文学>万里江山一片红国画山水作品 > 第十章 又是个丰年(第1页)
第十章 又是个丰年(第1页)
和家人守岁后,阿昭挑灯一盏回到了风和园,路过书房时,瞧见里面的灯还亮着,康烈正巧端着茶壶出来续水,忙唤她进去伺候,自己一个人窝在脚凳上打起瞌睡来。
她续了茶端到书桌边,见薛诤正伏案看着一卷地图,乃勃州的山川地形图,如此军事要献,昌宁侯竟尽数交予,可见对这个长子的厚望,她正看得入迷,冷不防薛诤一个侧头,两道目光相接,一个沉寂如渊,一个辰宿清耀。
阿昭没有闪躲,有时跟聪明人装傻才是自寻死路,她淡然自若问:“公子这是……要随侯爷去打仗?”
“斯然乱世,大丈夫投笔从戎保家卫国,有何不可吗?”薛诤合上舆图,举起双臂示意她宽衣。
阿昭为他解下腰带,道:“前线凶险,刀剑无眼,前儿夫人还把奴婢叫去她那里询问了您的近况,您若在战场上有个凶险,她和侯爷该有多伤心?”
薛诤闻言,凤眼轻眯,阿昭没看他的脸色,转身将外袍挂在了衣架上,左右她已经明里暗里向这位祖宗表明忠诚了,信不信随他吧!成天被人试探支使,累的是她好不好!
新年初一,天色未明,昌宁侯连子女的奉茶都没顾上喝,连夜收拾行囊去了军营。
早起,整个院子一片洁白,昨儿下半夜洋洋洒洒落起了白雪,六瓣飞出共梅花作舞,晨间成这一片空灵世界。阿昭穿了白毛滚边的杏黄色夹袄,下着同色棉裙,用白毛护耳裹住耳朵,宛若个清灵雪球,特带着香兰和香茗几个丫头去院中那棵最大的梅树下捡拾了干净的梅花瓣储藏在了一个坛子里。
这新春佳节瑞雪兆丰年,梅花也最是鲜艳,和着春雪储藏十天半月便可拿出来舂成花酱和做饼子吃,最是味美香甜,若有剩余,还可酿几壶梅花酒,埋在梅树下等到夏季炎热时拿出来解暑。
绿纱窗外,天与地共白茫茫一片,捧坛执梅的少女一身杏黄的袄裙慧黠蹲于树下,嘴角带着浓浓笑意,可谓色结烟霞,气冠山河,绝妙天生真颜色始露无疑。
康烈挠挠鼻梁,使劲咳嗽了两声,负手在窗前的薛诤移开了目光,他低头慢条斯理捋着竹青色镂金花纹束腰上悬挂的佩玉丝绦,康烈问:“公子,您刚才听到小的在说什么了吗?要不要……嘿嘿,我再重复一遍?”他说着闪身躲过了圣贤书的攻击,窜到一边嬉皮笑脸道:“嘿嘿,薛夫人请您早起去她那里用膳!”
薛诤没理他,自己披了黑毛大氅向门外走去。
开门时,乱风卷雪入鬓发,寒风吹在他冷俊的面容上气色依然,风雪中一身风华无限。香茗见状忙拿了油纸伞为他撑起,阿昭也上前几步捧着坛子站在廊下,探头看了看屋里的食盒未动,只听薛诤道:“今日初一,夫人唤我去她那里用膳,你做的这盒子吃食就赏了你和几个丫头了。日后做菜尽顾自己拿手的做吧,甜不甜,腻太腻,忒不可心!”
阿昭瞪大眼睛看着薛诤和一脸憋笑的康烈走远,良久都感觉自己听错了,什么叫“甜不甜,腻太腻,忒不可心”,这是说她做的东西难吃?从她开始捞大勺以来就不存在的好不好?
不死心的她走进屋里打开桌上的食盒,拣起一块芙蓉酥塞在了嘴里,甜而不腻,书软可口,比前些日子披星给她在外边铺子里买的不知道美味了多少倍,贵公子就是嘴刁!
她一个不耐烦摇头不经意看到了桌角的一块灰白色物体,蹲身将那东西捡了起来,据她多年经验辨形辨色,这是猪蹄膀的一部分,还是红烧过的,她不记得自己做过这道菜啊?有些烦躁的她没好气地把这烂骨头丢在一边,叫几个小丫头把屋子又重新打扫了一遍。
嘉庆居。
薛诤刚进正厅,才见百里慕卿也在,他手执一枝红梅,漫不经心把玩浅嗅,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无限,见到薛诤进来,连正眼也没抬一下。
薛诤目不斜视坐在了他的对面,下人奉了茶上来,莫离请百里慕卿用,他嗅了一下子,嗤之以鼻道:“好好的君山银针做什么佐放玉兰,固然增添了香浓之气,殊不知却掩盖了茗茶本味。古来香茗美酒自有真味,往往遇造作者投香物以佐,掩其真味,不以为糜,反以为佳,蠢矣。”
他越说越来劲,桃花眼一瞥厅外山石流水,更是清气一吐,“要说这园子的品味也是忒到家了,自古及今,山之胜多妙于天成,每坏于人造,这黄石盘的山石最重沟缝重横,形态玲珑,成于自然,做什么另做雕造,形于左右低矮中部山高,不止矫造,更正对中门阻了中流之气,自掩霉气!”
康烈站在薛诤身边,翻翻白眼嘀咕:“拧巴,费劲!”
莫离耳朵尖得很,气鼓鼓地站了出来,“大块头儿,你说谁呢?”
“谁接话说谁!”
“你……”
“我怎么了?”
“康烈!”薛诤瞄他一眼,康烈乖乖站了回去,他自顾拨着茶盏中的浮叶,才不管有些人的指桑骂槐!